
未被解放的农民诗人
本网记者 王玉琪
解放,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生活上的无忧,精神上的自由……然而,在为祖国解放作出无数贡献的沂蒙山区,却有这样一个人:一场浩劫,夺去了他的一切,从此他流落异乡,用血和泪写出串串诗行,向着巍巍的沂蒙山发出声声呼唤。
——作者题记
1988年4月,河北省满城县,在农民日报举办的“神星全国农民诗会”上,一位来自山东沂蒙山区的农民诗人引起了与会者与各家新闻单位的注意。人们赞叹他饱含深情、充满乡土气息的诗作,更为他几十年来的坎坷遭遇而感到震惊。《人民日报》、《中国农村经营报》、《北京日报》、《珠海特区报》的记者纷纷采访、约稿,保定日报和电台很快发表了他的作品。
他是谁?他就是1984年4月,被《农民日报》(当时为《中国农民报》)记者从山西吕梁山下一孔破窑洞里找回的农民诗人王贵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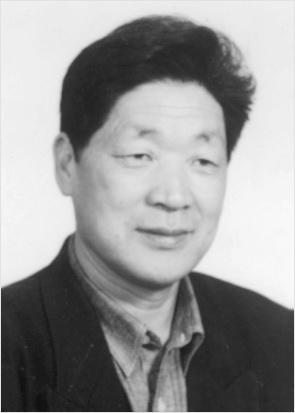
身归何处?行遍天涯路
1947年,王贵珠出生于山东沂源县金星乡太平官庄。当时,正值国民党大举进攻沂蒙山之时,刚刚出生三天的王贵珠便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了颠沛的生活。两年后,他的父亲随军南下福建,抛下他母亲和兄弟二人,并在福建另娶成婚。在他10岁的时候,哥哥结婚了,又和他们无情分居。从此,王贵珠便同母亲守着两间破草房,相依为命。
童年,王贵珠只读了四年零三个月的书,在他的眼里,世界本应该是美好的,就像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那样。然而,家里为什么那样穷?父亲和哥哥为什么会抛下他们?王贵珠想不明白这一切,她只知道母亲的命很苦,自己的命很苦。王贵珠开始自学了。一次,在垒地堰休息时,王贵珠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个“崽”字不认识,便向别人请教,哪知那人却嘲弄地骂了一句:“不要脸的狗崽子。”王贵珠强忍住泪水。晚上,他摸黑到邻村的孙老师家,孙老师告诉他:“骂你的那个字,就是那个崽呀。”王贵珠再也忍受不住内心的屈辱,泪水夺眶而出。
孙老师送给他一个小字典,从此,他就没日没夜地读起书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骤雨》、《草原烽火》、《苦菜花》等,他特别爱上了唐诗和千家诗。别人奇怪他为什么要看这么多的书,只有他心里明白,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崽”字啊!
1967年7月,王贵珠同周家上庄女青年王发兰自由恋爱结婚。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夺权不久,反逆流之风波及沂蒙山区。造反派硬说王贵珠家的成分是“富农”,王贵珠不服,他们就采取拉亲信、作伪证的办法,把王贵珠打成“反革命”。
“王贵珠啊王贵珠,解放前你家只有7亩地,土改时定为贫农,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是个任人欺凌的活寡妇,你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长夜漫漫,他陷入了苦苦的思索和探求之中。
他读书更加勤奋了。从1968年到1970年,在阅读了大量文学、诗词作品后,他以母亲为原型,写下了30多万字的小说《团圆梦》。然而,就在他奋笔疾书母亲的《团圆梦》之时,不料又面临一个残酷的打击。造反派对王贵珠家庭成分进行陷害,后调拨他的家庭关系,妻子无法承受这种精神折磨,先是闹离婚,接着竟把那30万字的《团圆梦》当作反革命罪证交出来,然后抛下刚刚出生23天的孩子,从此远走高飞。王贵珠为母亲做了《团圆梦》,却为自己留下一曲《长恨歌》。
泪眼望长空,长空尽蒙蒙。王贵珠这时只有两间空荡荡的破草房和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1975,他在别人家的鞭炮声中,开始了乞讨生涯。一家人总得活下去,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需要奶吃。就这样东家一口饭,西邻一口奶,勉强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这时,走了四个月的妻子回来了,带走了二女儿。而家里两口人的自留地,又被革委会强行收回,该给的口粮不发,该记得工分不计。王贵珠一家老小就这样熬呀熬呀,到了1976年,实在揭不开锅了,王贵珠就带着母亲和孩子前往福建,奔父求生。哪里想到,父亲因成分问题自顾不暇,竟将他们拒之门外。
王贵珠带着一家老小,含着眼泪离开了福建。他们一边乞讨,一边漫无目的走村串巷,路上,在一位好心人的厨房住了下来。此时,王贵珠望着饱经沧桑的母亲和怀里啼哭的孩子,心都要碎了。母亲千里寻夫,儿子千里奔父,可天下之大,竟无他们一家人的容身之地,悲愤之情油然而生,借着木板墙壁透过的光纤,王贵珠以母亲的口吻写下《钗头凤·乞妇吟》:
人间共,别离痛,古今多少团圆梦。儿无父,孙无母,水流容易,光阴难度。怵!怵!怵!
香莲径,含羞碰,乞生之路莫前定。家乡雾,他乡露,天涯流浪,命归何处?步!步!步!
古往今来,离愁别恨千千万万,然而有谁能像王贵珠这样一家三代重叠?又有哪一个家庭是这样的,有父而又无父,有母而又无母,有夫而又无夫,有妻而又无妻,有家而又无家啊……
就在这时,听人说山西好落户,王贵珠便用一辆平板车拉着母亲和孩子,向山西进发了。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在连绵起伏的吕梁山脉,有这么一空破窑洞,往前、往左、往右,几十里外没有人烟,往后,三里路外才听到人的声音。它就是这么寂寞而孤独地立在这群山之中。1977年的10月,王贵珠全家经过一年的乞讨、跋涉来到这孔窑洞前,在山西吉县屯里乡庄子村落了户。
总算有家了。王贵珠安下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在黑漆漆的窑洞的暗窑壁上掏出一个脸盆大的洞作窗户,然后支上几块木板,当作他的书房。他要在这里记下一路上的风土人情;他要整理写在从路边捡来的纸上的诗稿;他还要好好地读一读书,读那些用路上乞讨来的钱买的唐诗、宋词……
总算有家了。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他除了每天要走二里多路去完成村里的农活外,便在这荒无人迹的山崖下开荒、放牛、刨甘草、采连翘,换来点钱,除了买盐、买煤油,便都让王贵珠买了书和纸。穿的衣服、鞋是从废品收购站的好心人那里要来的,他抽的烟则是山上一种叫土拉木的树叶……
总算有家了。这时的王贵珠,却更加怀念那沂蒙山中的两间破草屋。多少个黄昏,他仰天长叹,多少个夜晚,他孤枕难眠。沂蒙山啊沂蒙山,此为异乡客,何日能重归?
就这样,一家四口相依为命,终于到1982年,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这孔破旧的窑洞门前。这年,村里搞起了承包,他一家承包了28亩土地,还喂养了一头村里作价给他的牛,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转了。这时,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农家生活的日渐富裕,激发了王贵珠心底多年的创作欲望,他的诗歌,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思想境界。他在一首《重阳》诗中写道:
农家几曾度重阳,一任西风说短长。
敢望耕耘能自主,休夸收获比人强。
醒神红叶层层艳,疗毒黄花处处香。
此日登高多逸兴,只缘光景不寻常。
然而,正当王贵珠满怀希望走进新生活之际,又一场灾难从天而降。这一年,他舅舅家的一个表弟来到山西,母亲见到娘家侄子,亲得恨不能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王贵珠给表弟在当地找了个对象。这时,王贵珠的母亲正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举目无亲的王贵珠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四处抓药,找医生,甚至为母亲备下了寿木。而就在这关头,那个表弟却带着女方不辞而别,远走高飞。女方的父母硬把责任推到了王贵珠头上,强行牵走了他精心饲养的那头牛,村里的某些人又收回了他承包的土地,并要赶他走。母亲经受不了如此变故,一气之下,昏迷不醒。整整四天四夜,王贵珠一边守在母亲的床前,一边焦急地盼望山路上响起的牛铃声,孩子在山上放牛,山上荒无人迹,有狼,还有蛇……四天之后,母亲终于醒过来了,却一年没能下炕走动。
生活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王贵珠怎么也想不到,自打他降临人世,他要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他要抗争了,他想起苏武牧羊的故事,在诗中他写道:
晴川浮积雾,寒谷晚回春。
更怀苏北海,持节树雄心。
1983年春天,王贵珠带着8岁的儿子和他用血和泪写成的诗稿,一路行乞,登上了上访之路。他到了太原,又到了北京。人们看到他们父子蓬头垢面的样子,连理都没理。他又带着儿子,到了山东沂源县,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然而等待他的则是一个无情的打击:他的户口早已被当地取消。
他成了黑人黑户。王贵珠此时的心中在流泪,在滴血,他愤然写道:“一经文革改成分,走遍天涯是黑人。活该寒霜铺地卧,应当骤雨劈头淋。”他不停地上访,不停地写诗。诗,成了他几十年来的精神寄托,“待到神州明日月,祖孙能不喜逢春”。诗里,融进了他多少情感,多少希望。
1984年3月,王贵珠的处女作《绿化吕梁》在山西临汾报上发表了:
吕梁植被几经残,除却荒山是秃山。
去日西风愁断绪,年来春雨喜连绵。
保苗哪得天公与,营造多凭花果钱。
待到高原成绿海,乡村无处不桃源。
而在这时,他的上访信也有了回音。正当他高兴地等着上级派人来了解他的情况时,却不料一些人竟当着乡村干部的面,解救撒疯打得他口吐鲜血……
暮鸦叫长空,狐兔归巢狼出征。百草萧萧千木号。
西风,多少天涯游子情。
身上冷如冰,霜结寒窑到五更。儿女询宗娘念旧。
诗成,人眼不明天眼明。
“人眼不明天眼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漂泊不定,给王贵珠的心灵带来巨大的伤害,此时,他多么盼望一双正义之手。有人告诉他,咱们国家出了个农民报,或许能给你伸张正义。怀着一线希望,他给《中国农民报》编辑部寄来了一封信和30首诗稿。
醒了,思乡的梦
1984年4月20日,对于每天忙忙碌碌生活着的人来说,或许是个极平淡的日子。然而,在吕梁山下那一空破窑洞里,这一天却成了王贵珠一家人永生难忘的日子。《中国农民报》的记者在县委宣传部和乡领导的陪同之下,步行15里,推开了这孔破窑洞的门。当记者握住王贵珠的手,叫一声“王贵珠同志”时,这位走遍天涯的游子的周身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几十年的历尽坎坷,听到的只有反革命、狗崽子的叫骂声,何尝听到过如此亲切的呼唤?王贵珠手足无措,浑身颤抖,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哭够了笑,笑够了哭,泪水和着笑声,流出了多少辛酸,多少喜悦!
接着,报社记者偕同王贵珠回到了山东省沂源县,县委认为,如何处理王贵珠所反映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王贵珠本人的命运,而且还关系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对此,县委组织了由县纪委、宣传部、信访科、县法院、民政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王贵珠反映的问题属实。县委书记韩修民、县长冯学训当即表示:欢迎王贵珠回故乡。
1984年5月27日,中国农民报刊登了王贵珠的来信《苦尽甜来——一个业余农民作者的经历》和记者的调查附记;6月6日,刊登了沂源县委、县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理结果,同时刊登了王贵珠的诗《醒了,思乡的梦》:
党报传信,县委欢迎,
亲朋相会,父老重逢
……
故乡啊,莫非又是蜃楼的幻影?
慈母念旧,儿女询宗,
天涯漂泊,泪溢成冰,
……
多少回,睁开睡眼却身在异境。
愁付流水,恩自党风,
尽千钧力,写再生情。
……
醒来了,我心中那思乡的梦!
8月25日,日本刊物《日中农交》全文转载了王贵珠的这首诗。
1984年10月,王贵珠一家告别了为他们遮风挡雨8年多的那孔破窑洞,踏上了回故乡之路。吉县县委专门派来两辆专车,把他们全家送到临汾火车站,庄子村的一名干部一直把他们送到山东沂源县。
沂蒙山,梦回萦绕的故乡,浪迹天涯的游子回来了。一路之上,王贵珠按奈不住内心的喜悦,看呀,写呀,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写进他内心的喜悦之中:
游子故乡行,这回非梦中。
蜂吟槐树岭,人笑石榴坪。
雨润山川秀,风和天地明。
忽闻乡土调,双目顿盈盈。
沂源县有关部门马上纠正了他的成份问题,并安排他在县文化局作为计划内临时工,一有时机,立即转正。1985年10月,县政府给他分了房子,他同前妻在法律上办了离婚手续。不久,王贵珠又重新组织了家庭,妻子叫李振英,是个心地善良的女性,当时只有27岁,她为王贵珠几十年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打心眼里爱上了他。
重获新生的王贵珠,把他对故乡的眷念,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追求,全部情感融于他的笔下,那是他心底的歌声啊。1984年12月,他的散文诗《沂蒙花椒》荣获《中国农民报》国庆征文三等奖。在这篇散文诗里,王贵珠从心灵深处唱出了他对沂蒙山的炽热之爱,他写道:“看着眼前如霞似火的花椒林,我不禁潸然泪下。沂蒙山的花椒啊,人们想你、盼你多少年,如今,你终于又在沂蒙山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我真想再唱一曲沂蒙颂!”
在他的《七律·老农夜饮》中,他以充满乡土气息的笔调,热情赞颂了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
何能衣食不成愁?杯酒入心话哽喉。
人道中年难过富,我经半世喜从头。
全新彩电孵鸡奖,一色砖房植树酬。
仙女若知应赞叹,神州今比昔情稠。
从1984年3月至今,王贵珠已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作近20首。
今年4月,当王贵珠接到《农民日报》举办“神星全国农民诗会”的邀请信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在赴河北满城的路上,他信笔写出了自己心底的激情:
赤字心声,慈母音容,多少年水叠山重?
农民诗会,更是难逢,激心花儿放,心潮儿涌,
心眼儿灵。
赴约途中,特别飞快,望川原一片葱茏。
更怀亲友,临别叮咛,写新生的恩,终生的愿,
再生的情。
本不该留下的问号
当我们的情感随着王贵珠一家重新回到沂蒙山时,我们的心里却感到异常沉重。王贵珠几十年来所经历的磨难,并不能只代表他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许许多多经历了那场浩劫的人和事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应该牢记那场浩劫。
我们之所以感到心情沉重,是因为我们了解到王贵珠目前的状况。
我们翻阅了《农民日报》1985年7月20日刊登的《沂源县委关于王贵珠一案的答复》,其中对“文革”中迫害王贵珠的主要当事人的处理决定为“留党察看”。而且县委认为,“处分决定是在充分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事求是的。”然而,这位当事人却在后来四处告状,说王贵珠是欺骗县委,自称是农民诗人。而令人困惑的是,就在“答复”见报不到半年时间,县纪委又作出对当事人不予处分的决定,并重新落实的政策。
王贵珠一回到家乡,被安排到县文化局的计划内临时工,时间过去快四年了,他仍然是个计划内临时工,“答复”中所说“何时地区有正式职工指标下达,立即将王贵珠安排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却成了一句无懈可击的官话。至今,王贵珠一家5口人只靠他和大女儿加起来不到150元的工资去买高价粮来生活。
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工作,王贵珠虽然结束了多年颠沛生涯,可他的心却仍然在流浪、漂泊。我们又重新回想其他写的《苦尽甜来》,苦真的尽了吗?甜真的来了吗?他是否身心都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我们有想到山西吉县,当县委书记了解到王贵珠的经历后,马上指示宣传部为他订了4份报纸,让民政局解决每月50元的救济款,让庄子村退还承包地核耕牛。他还亲自到新华书店,为王贵珠买了一部《辞通》。
当王贵珠要离开吉县时,县委书记极力挽留,并要为他安排工作。然而王贵珠却婉言谢绝。毕竟“月是故乡明”啊!
我们无意把两个县做一个比较,我们只是画出了几个问号!
在这次农民诗会上,主持会议的农民日报副总编梁振明对王贵珠说:“《农民日报》是为农民说话的,你是个农民诗人,时至今日,实际上仍然是个未被真正解放的人。报社的许多人都很关心你。”
也有人问王贵珠,时至今日,你对从山西回到山东又作何感想?
王贵珠笑了笑,沂蒙山,那是家啊!
沂蒙山啊沂蒙山,你听到了吗?



农民日报社主办,中国农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2019- by farmer.com.cn.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