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秀莹,作家,《中国作家》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旧院》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其中《陌上》荣获施耐庵文学奖,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6)、《收获》文学排行榜(2016);《他乡》荣获十月文学奖,荣登201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9);《野望》荣登202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文学评论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七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年度好书榜,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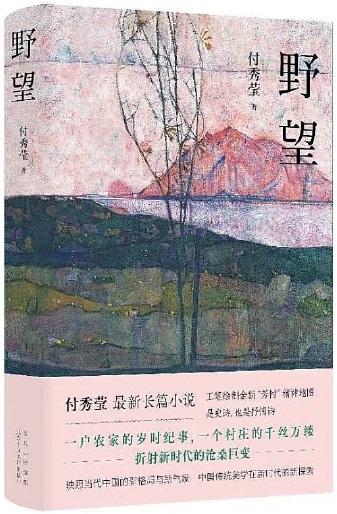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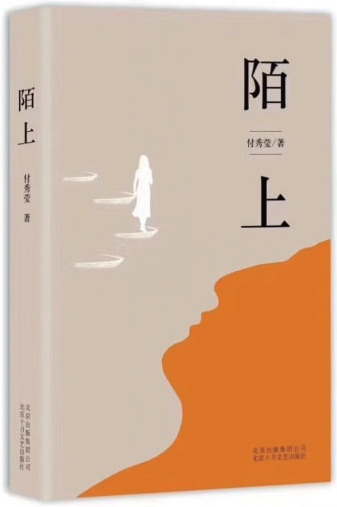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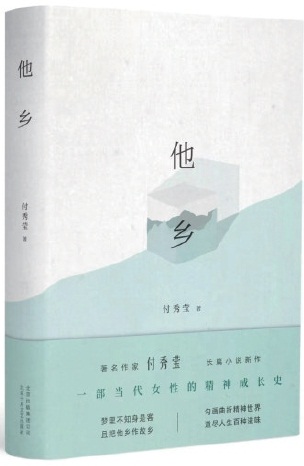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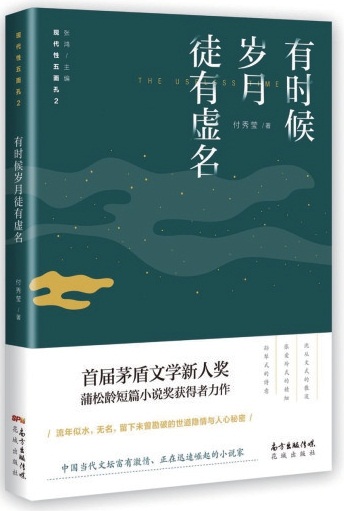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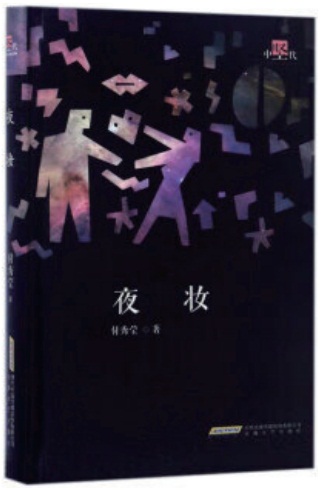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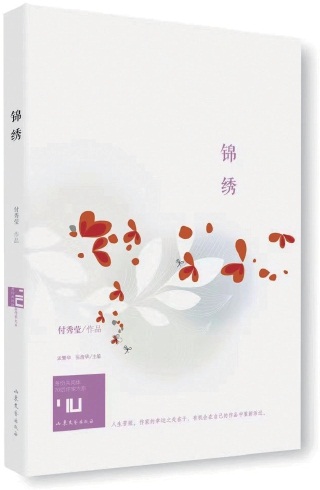
我必须承认,我是幸运的。
作为写作者,我得以跨越万水千山,
隔着重重光阴,沿着文字的小径,
一遍又一遍重回故乡,重回我的村庄,
与我的亲人们重逢,谈笑,相拥而泣。
我出生在华北大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太行山以东,滹沱河畔,在我的小说里,叫做芳村。当然是虚构的名字。我的村庄另有其名,南汪。在我们县城以南,大约十几里路吧。实在是最平凡不过的北方乡村,偏远,安静,民风淳朴。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没有什么起伏,开阔而旷远。大多种麦子,玉米,棉花,大豆,谷子也种,谷田里常常立着稻草人,吓唬那些偷嘴的鸟雀们。大平原上风来雨去,庄稼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四季分明,干脆利落。

付秀莹(右一)和父亲、姐姐在老家院子。
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度过了天真无邪而又懵懂混沌的童年时代。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字也写得好,算得上乡村知识分子吧,颇受人敬重。我很记得,家里常有那种厚厚的账本,纸张挺括,蓝的红的格子,上头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母亲呢,识字不多,却心地仁厚,端正秀丽,又是个极热心热肠的,人缘颇好。母亲爱干净,家里家外,都拾掇得干净清爽。我们姐妹几个,也被她巧手打扮,走到人前,一个个整齐体面。家里头常年串门儿的不断,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大多是妇女们,也有做针线的,也有捡豆子的,也有只来扯闲篇的,唧唧喳喳,笑语喧哗。母亲笑吟吟的,招呼着款待着,是女主人的大方洒落。不知道说到什么,人们都笑起来,风摇银铃一般。阳光金沙一样漫漫落下,风从村庄深处吹过,一院子树影摇曳,满地铜钱大小的光斑晃动跳跃。我坐在门槛上,被这人世间的繁华热闹深深吸引了。我不知道,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年幼天真,尚不知世事,而父母在堂,人情甘美。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在乡村的蔽护之中,尘世的风霜还没有落在我身上。我在村庄里疯玩,在田野里奔跑,上树摘枣,下田摸瓜。麦子扬花了,玉米吐出紫红色的缨子,谷子垂下饱满的脑袋,棉田里棉花白茫茫一片,仿佛下了一场大雪。这慷慨无私的土地,年复一年,用累累果实回馈人们的辛劳,用收获的喜悦报答人们的诚实付出。草木生长的潮湿气息,夹杂着新鲜泥土的腥味,淡蓝色的炊烟升腾起来,饭菜的香气在村庄里缓缓流荡。母亲在呼喊孩子回家吃饭,一只狗忽然叫起来,而不知谁家的娃娃呀呀哭了。这鸡鸣狗吠烟火漫卷的人间呀。
如果用色调来描述的话,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是淡淡的金色。我的村庄在淡金色的光晕里若隐若现,时而清晰,时而恍惚。大约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对我格外偏爱一些。我上面有两个姐姐。照说,我的到来大约该是令人失望的吧。在当时的乡下,有很强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我呢,也似乎知道自己的不受欢迎,小小年纪,便格外懂事。心思纯净柔软,心疼父母,体恤亲人。乡下吃饭多用一种矮饭桌,一家人围坐,也有蹲着的,因为坐物不够。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把小板凳让给父母,自己蹲着。小小的人儿,还站不大稳当,歪歪斜斜勉力蹲着,常常就一屁股坐在地下了。那时候,母亲多病,家里有好饭食,也知道让给母亲。有一回,母亲狠心吃下半碗蛋羹,把另一半给我,我一面悄悄咽着口水,一面把碗推开。母亲默默流泪,恨道:“多大的孩子,怎么就叫我得了病。”如果说我的童年记忆里有些许阴影的话,大约便是母亲的病了。多少次,在外头玩累了,一路跑回家,进了院子,喊母亲,见她在炕上躺着,一颗小小的心便揪起来。我常常守在母亲身边,不大肯出去玩。也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细腻,多思,爱幻想,心头常常无端涌起淡淡的忧愁来。乡间寻常的日升月落,风吹草长,都令我久久流连,内心激荡。母亲对此很是担心,觉得我不似人家的小孩子活泼欢快。及至后来上学,也不大肯催逼我读书,反倒是常撵我出去玩耍,怕我累坏了脑子。我至今依然记得,有一回,我把被老师表扬的一篇作文读给她听,她靠在炕上,听得认真,微笑着,眼睛弯弯,嘴角弯弯,是欢喜的意思。那神情姿态,我总也忘不了,记了这么多年。
父亲爱酒。在我们乡下,男人大多好饮。街上见了,打招呼的话就是,哪天咱喝点呀。喝什么呢,当然是喝酒。这地方人性格豪爽刚正,有那么一点燕赵之地的慷慨悲歌之气。酒量好,酒风也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醉倒便显不出情深意重,不醉倒便没有尽到待客的礼数。父亲喝酒是村里有名的。婚丧嫁娶,拜寿庆生,酒自然是少不得的。很小的时候,饭桌上,父亲拿筷子蘸了酒,往我嘴里抿一抿,我竟然咂咂有声,手舞足蹈。母亲嗔怪,父亲却朗声大笑。我想,父亲一生无子,大约是把我当作儿子来养了。我们乡下,女孩子是不上酒桌的。但我是例外。陪父亲喝酒,是我童年记忆里明亮而热烈的段落。姐姐们笑我,叫我假小子。长大后离家,在故乡和他乡之间往返奔波,山一程水一程,人生的风雨也曾经历,命运的烈酒也品尝过。与父亲对饮,似乎成了我们父女团聚的一个重要仪式。而今,父亲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早已步入他的暮年,每次回乡,我依然会不顾医嘱和姐姐们阻拦,给他带酒。父亲微笑着,神情柔软。我不知道,当他看见酒,是否会想起很多往事,想起时光流逝,岁月忽已晚。
多年以后,当我提笔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我写了我的村庄。记得芳村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我的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里。“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父亲在离家几十里的镇上教书。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两个,住在村子的最东头。这个村子,叫做芳村。”当时正是北京的盛夏。我住在北师大附近的一栋老楼里,二层。窗外,树木繁茂,蝉在热烈地高声歌唱。我忘情地写着,几乎是一挥而就。我再也想不到,这篇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将成为我的成名作,引领我从此走上写作之路。而小说里的芳村,这个随手写下的村庄的名字,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地理,成为我艺术想象的源泉,创作激情的策源地,日后陪我走过漫漫人生长路。在《爱情到处流传》中,我写了父母之间的乡村爱情,朴素温暖,而又惊心动魄。小说里的父亲,也是乡村知识分子。而母亲,风姿秀丽宅心仁厚。小说当然是虚构。然而,谁敢说,虚构的故事里没有现实人生投下的重重叠叠的光影呢。当熟悉的不熟悉的读者朋友们,怀着各自心事,关切地问候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大约是把现实和虚构混淆了。我微笑不语,并不忍说破。我猜想,或许,他们问候的并不是我笔下的人物,而正是他们被命运风暴冲刷之下真实的自己。
在中篇小说《旧院》里,我开篇写道,“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旧院指的是我姥姥家的大院子”。这是真的。我姥姥家的院子,就在我家后面的过道里,我们叫做旧院。谁的童年经验里没有“姥姥家”的记忆呢?姥姥家,或者外婆家,象征着温暖,亲情,爱,人生之初一切美好的事物,慈爱,包容,笑声,怀抱,食物的香气,热气腾腾,而又明亮迷人。在《旧院》里,以及在《笑忘书》《锦绣年代》里,我记下了旧院里的人和事,一个家族的繁华盛世,以及在时间流逝中,她的无可挽回的风流云散。原本是想着写旧院系列的,后来却不了了之了。至今想来,犹觉遗憾。而今,随着去年百岁姥姥的离世,以及《旧院》中的重要人物舅舅的随之远行,日渐沉寂冷清的旧院,早已不复昔年盛景了。今年国庆节回乡,我满怀踌躇,竟不忍去旧院看一眼,我不是怕踏进旧院的门槛,而是怕那种独立清秋、茫然四顾的今昔之感。值得安慰的是,我终究是写下了《旧院》,我终究是用文字留住了生命中那些值得珍重爱惜的情感和记忆。
在长篇小说《陌上》中,第一次,我有了为我的村庄立传的念头,或者你叫做野心也好。多少次,我在村子里转来转去,看望每一棵庄稼每一棵野草,触摸每一滴露珠每一声鸟鸣。我踏着月光星光,走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多么神奇呀。当年,我怀着如此强烈的念头,一心要离开村庄,离开故乡,到城里去。而今,我这个故乡的逆子,在异地他乡,在别人的城市,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吃了那么多的苦头,终于还是回来了,并且,我要用手里的笔,写出村庄的此时此刻。我的芳村,有多么偏僻就有多么繁华,有多么狭窄就有多么辽阔,有多么遥远就有多么切近,有多少虚构就有多少真实。我几乎是挨家挨户写起,以散点透视的笔法,写村庄里的鸡鸣狗吠,生老病死,时代激流深处,人的心灵变迁和精神安顿。我试图写出一个村庄的隐秘心事,写出乡土中国在历史洪流中的波光云影,继而写出一个时代的山河巨变。
后来,我写了长篇《他乡》。小说中,我以从芳村走出的女性翟小梨为主角,写她从乡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一路走来,她的生命经验与精神成长,城市与乡村、个人与时代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这是《他乡》封面上的一句话,颇堪玩味。《陌上》里有一句话,是不是,回不去的,才是故乡。翟小梨其实是《陌上》最后一章里一个人物,众多人物故事中一掠而过。在《他乡》中,我让她做了主角。从芳村出走的一代知识女性,在他乡、在城市,在肉身安顿和精神流徙之间,艰难地与生活达成和解,最终获得内心安宁。这些年,我一直在面对由《他乡》引出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不是翟小梨?谁是翟小梨?我想说的是,亲爱的读者朋友,我是不是翟小梨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你在翟小梨身上照见了自己诚实的内心,就是对我,对一个作家最大的安慰。
《野望》是我最新的一部长篇。还是那个村庄,还是那芳村里那些人,翠台,素台,喜针,小鸾,根来,大坡,小别扭媳妇,臭菊……她们在芳村走来走去,哭了,笑了,恼了,爱了,家务事、儿女情缠绕,家事、国事、天下事交织。我以传统的二十节气统摄全篇,每一个节气为一章,全书共二十四章。四时流转,季节轮回,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变,而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平凡普通的日常绵长温暖,他们创造的生产生活实践生生不息。《野望》里的那些人物的名字,其实就是我的乡亲们的名字,我信手拈来,觉得亲切有味。他们那些带着泥土露珠的语言,那些血肉饱满的生活细节,那些乡下人的幽默风趣,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小心思,意味无穷,不足为外人道,几乎原封不动被我抄录下来。读者惊叹,在城市这么多年,竟然对乡村如此熟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不过是生活的记录员罢了。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野望》的写作,令我更加深切地体味到,生活是创作的活水源头。只有深入到火热的时代生活现场,潜入生活激流深处,才有可能触摸到时代精神的秘密。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一篇创作谈《痛饮生活的泉水》里,我写道,在《野望》的写作中,我是忘我的,忘记了我的作家身份,忘记了那个自以为是、肤浅幼稚的“小我”,满心满眼,纸上笔端,都是沸腾的乡村大地,是明月星辰下沸腾的人群,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长河里的浪花飞溅。我得承认,是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洗涤我、修正我、塑造我、成就我。写野望,我是信笔直书。我大口痛饮着生活的泉水,第一次品尝到别样的新鲜的滋味——自然的,朴素的,真实的,繁华落尽,如同广袤丰厚的秋天的大地。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书写我的芳村。我笔下的人物,都跟芳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或者生活在芳村,或者离开芳村到城市去,更有甚者,是离开之后重新返回,是芳村的返乡者。芳村,已经成为我的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地标。从这个意义上,我与芳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互的,书写与被书写,虚构与被虚构,阐释与被阐释,塑造与被塑造。《陌上》《他乡》《野望》被评论界称为“芳村三部曲”,也早有研究者关注我的“芳村叙事”。常有朋友玩笑,什么时候到你们芳村去看看?是啊。我们芳村,我亲爱的芳村。离家这么多年,对我这个故乡的逆子,我亲爱的芳村一直在无私地包容、给予、馈赠、成全。我不过是故乡大地上一棵平凡卑微的小草,是那片土地以及深扎其中的根系,令我有了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可能。
我曾经在《学习时报》上发表过一篇长文,是报纸命题,《我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想来,多年来对中国乡村的持续关注和书写,对芳村文学世界的不断建构,令我的创作与乡村大地、乡土中国生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我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正是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一切,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句方言,一个乳名,一滴汗水,一声咳嗽,哺育我、滋养我、教化我、启迪我。我的故乡大地,是我的来处,亦是我的归处。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我灵魂的栖居之所,也是我流浪远方多年、顿挫跌宕而不致迷路的秘密。我必须承认,我是幸运的。作为写作者,我得以跨越万水千山,隔着重重光阴,沿着文字的小径,一遍又一遍重回故乡,重回我的村庄,与我的亲人们重逢,谈笑,相拥而泣。我当然是幸运的。通过写作,我有机会记录下故乡大地上经历的种种,沧海与桑田,悲欢与聚散。时代列车轰然驶过,我愿意在尘埃尚未落定的时候,细心捕捉那些奋力奔跑的身影。当现实人生千差万错来不及修改,当时光如逝水岁月之矢呼啸而过,当万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还好有写作,幸亏有写作。感恩生活,感恩故土大地。我以写作向我亲爱的芳村致敬。
作者:付秀莹



农民日报社主办,中国农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2019- by farmer.com.cn.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