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能找到的拉呱人多是上了年纪的,话题大多涉及更早的年代。夏天的夜晚,我们摇着蒲扇,直聊到月上树梢。冬天,我们守着火炉聊,直到传盘星爬上邻家楼头。
前年年初,我将长篇小说《蚂蚱》投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就收到回信。信中有编辑相当热情的评语:《蚂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鲁南地区乡村社会微观历史的再现,以今天的视角重现昨日乡村人物的精彩,有《清明上河图》的意趣,更有蒲松龄聊斋文化的况味。曾经的蚂蚱庙村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缩影,人们守着土地苦熬岁月,豪杰如流星转瞬即逝,知识阶层混沌笼统,村民卑微如草芥。在天灾人祸一轮一轮的冲击下,人性的善恶、生命的挣扎令人叹息。《蚂蚱》切开了那个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正内核……

作品被出版社肯定,总是快乐的,况且,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我的乡村生活的一件副产品。小说出版后,周围的朋友不无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写的,此前怎么一点信息没流露?我借用一首馍馍店老板的歌,开玩笑说:“拾来的麦子借来的磨,大风吹来的柴禾垛,哄着孩子做的馍——卖一个,赚一个。”此书从动笔到几次修改,前后虽然用了十年工夫,但它确实是顺手捡来的——那是自己的先人很久前遗落的。
一切都来自生活的顺变
这本书的生成,和我十多年的乡居有关。我的回乡并非故意的人设,而是一步一步“陷落”的。多年前,母亲每逢冬天都要到北京避寒,春天则要回乡下,像只候鸟。有两个农历的节气是她十多年一直遵循的迁徙日期:冬至和清明。冬至,出嫁的女儿要到娘家上坟,向曾经养育自己的父母“送寒衣”;清明的祭扫,则是给我逝去的父亲送些“钱帛”,别让他在“那边”的日子过于拮据。去京之前,回村之后,我得陪她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自然就有了耳闻目睹的乡村现实,这些现实让我心绪难平,于是促生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问故乡》。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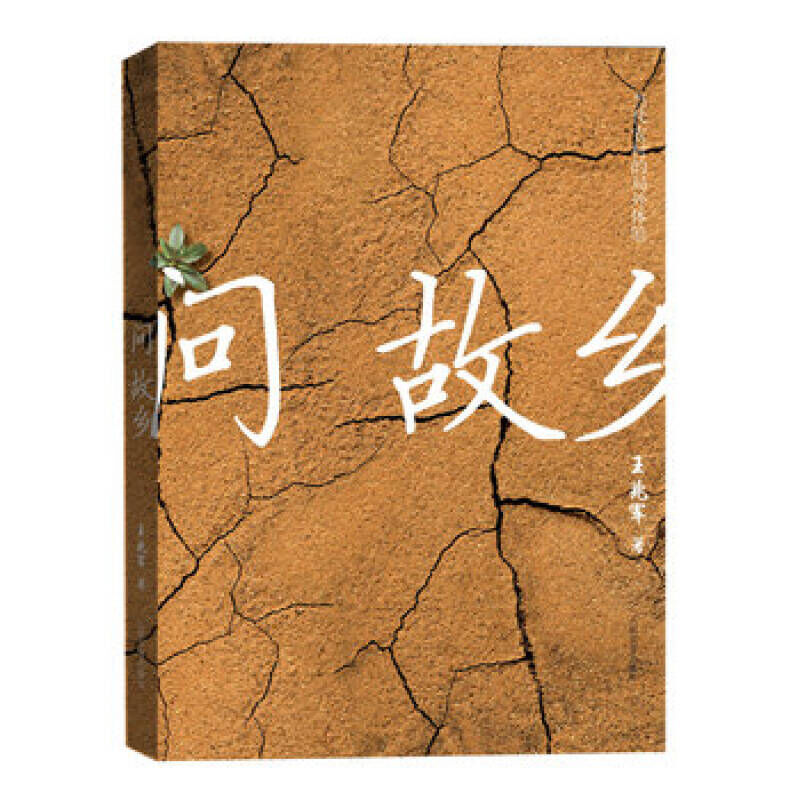
在《问故乡》中,我不无悲情地描述了当代农民生计的艰难,环境的脏乱,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凋敝。乡亲们看了那本书,说我:“你不能光批评啊!”言外之意,你得做点建设性的事情呢。退休后不久,我母亲去世了。守丧期间,独坐荒村院落,面对夜空寒星,我想,这里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是得为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能力不在大小,出一份力就好。根据自身能力和局限,便生出办个书院的想法,众人皆曰可。既然办书院,就得有几间房子,有课桌,有教材,还得有个阅览室。要弄齐这些最基本的配置,也需要钱,而我的积蓄太少,不得已,就接了一些文字的活,陆续写了两本村史:《黑墩屯》和《朱陈》,还有两本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故事的《春秋故城即丘》和《乱世之花——文姜传》,后边这三本书挣了一些钱,暂解燃眉之急。后来我又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中《王羲之传》的写作。因为这本书,我自己走上了书法和绘画的路,书院也得以运行。
书院很小,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图书室,有媒体称之为中国最基层也是最小的书院。那段时间里,可谓惨淡经营,筚路蓝缕,身心俱疲,幸亏家人和朋友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乡亲们也在劳作中给我很多帮助。开课的日子里,白天是忙碌的,忙得连口热饭都顾不上。但是到了夜晚,除了青灯一盏修订教材,其他时间便是无边无际的枯寂,实在无由打发,就去找乡亲们闲聊。我这年纪,长期在都市生活,和当代农村已经相当陌生,即使是出身本村本地,也很难和年轻人沟通。我能找到的拉呱人多是上了年纪的,话题大多涉及更早的年代。夏天的夜晚,我们摇着蒲扇,直聊到月上树梢。冬天,我们守着火炉聊,直到传盘星爬上邻家楼头。有一次,聊天到午夜,我沿着汪塘旁的小道踽踽而行,被一位喝醉酒的人撞飞,差点丧命。在那些翻动历史尘埃的闲聊中,我逐渐将先辈的往事连缀起来,像是久远之前的幻灯片。在那里,我看到先人们经磨历劫的过去,看到他们悲欣交集的生活,听到“三座大山”下妇女们的控诉,领略了旧时读书人的苍凉,发现了新思想萌发的社会基础,等等。我仔细咀嚼那些故事,体察当年的各色人物,感慨之余,写成文字,就有了长篇小说《蚂蚱》。现在想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如同宿命。
一段微观历史的悠远回声
小说构思之初,我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构建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写出来像那么回事。以前虽然写过几部长篇,但所描述的大都和我个人的现实见闻相关,如今要构建未曾涉足其中的晚清民国的社会生活,只能靠想象,而想象的基础只能靠充分的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是一个让人杂色纷披的人性表演场,许多人物虽有不乏精彩的故事,但那些故事并不连贯,英雄转瞬即逝,为此,我只能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去描摹他们。《蚂蚱》刻画了几十位人物,有的人先知先觉,以不变应万变;有的人蒙昧麻木,被动接受潮流的冲击;有的人顺应趋势,随时变换角色定位;有的人抱残守缺,只能在“乡愿”梦想的破裂处遁入烟尘……他们都有自己的光芒和地位,没有几个人能占据全篇。近代中国北方农村较少大家族,也较少影响久远的人物,升斗小民很难拥有连续性的传奇,为了防止情节上的断裂和违和感,我只能依赖细节,依赖他们彼此间起承转合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勾画出来,让卑微的生活多少拥有美学上的辐射,诚如本书责任编辑所说:《蚂蚱》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
原生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的,很难用非黑即白的方法处理。农业社会的衰落,生产方式的老旧,新思想的萌芽,传统思维与新时代的碰撞,体现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纷繁迷乱,难说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当年的农民,因其在经济、身份、婚姻、家风、教育、技能诸方面的不同,表现出大相径庭的人生轨迹。他们质朴,但也粗粝;他们善良,但也愚昧;他们向往美好,但命运多舛;有些人看上去生性顽劣,其实多半是社会的责任;许多人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做过努力,但田园牧歌始终只是一种幻象。不论是谁,他们在不同阶段都展示出生命固有的能量。生活本身虽然精彩,但若以浮光掠影的文字去描述,则会流于自然主义。我不甘心止步于历史故事的简单书写,尝试以几近魔幻的方式对既存素材加以升华,让“蚂蚱”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我试图用“蚂蚱”这一意象让一段微观历史借助文学发出悠远的回声。
书一出版,就引起广泛注意。有评论家认为,小说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对民国时期乡村生活题材的描述(如民国初年的乡村集市,如乡村绅士的行止名状,如殷云舒的走婚,瘸造杀人等),所构建的意象在当代同类作品中独具一格(如乡村社戏,如庙宇的存亡,如神灵的地位等)。作品中那些陌生的人物给中国的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形象(如抹斗手谢芳春,如约地贾三福,如底层知识分子赵琪,如个性张扬的宋氏,如小短辫的人生箴言,兵痞扈永等)。这些肯定让我感到欣慰。
 王兆军(左)和老乡聊天。
王兆军(左)和老乡聊天。
在写作中,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女性。为了争取婚姻自由而大声疾呼的宋氏,最终死于贫困,尸体横躺在茅房的冰雪之中。王姑娘爱上艺人解信德,爹娘甚至连一件棉袄都要从女儿身上扒下来!谢殿章的妻子本有自己的意中人,被迫嫁人后,因拒绝同床,竟被男人当众暴虐。书中另一个女性殷云舒的命运,更加令人唏嘘。她嫁给了一个性无能且智障的男子,当众被羞辱后离家出走。但无路可去,在旧伦理的绳捆索绑中,她像一个被剥夺了所有幸福的佣人,每天奔走于娘家和婆家之间的荒野上,看不见一线光明。众人将这位美丽女子的悲辛当作风景,却无人体会当事人心中汹涌的苦水。为了将这个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描述出来,我有意采用了从容平静的笔调,细致而简约地书写当事人内心巨大的隐忍和极度的克制,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给这位冰清玉洁的女神以充分的尊敬,质朴内敛的文字更能形成阅读的冲击力。
沉下心来想想,这里发生的一切苦难,都来自这片土地,被腐朽文化毒化的、被剥削制度抽干营养的、粗陋而贫瘠的土地!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低质的生活方式,只能生长这样的族群。巴金先生说过:深究这个族群的思想,这里的人们配得上他们所遭受的所有苦难。蚂蚱既是害人的精灵,同时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二者互为因果。蚂蚱庙的芸芸众生之所以还能生生不息,依赖的就是生命本身的欲望、能量和毅力,而这正是旧制度所忽视的。正是这样的文化土壤,培育出各色各样的与之呼应的人物。贾三福的左右逢源,赵建章的呼风唤雨,大练长的颟顸短视,谢芳春的暧昧优柔,胡寡妇的残暴凶狠,扈淑廉的粗陋好赌,林宗申的两面为人,念过孔孟程朱的读书人迂腐猥琐,只有赵琪和解信德算是坚持了自我的人。前者相信“不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成为拒绝与潮流合作的孤勇者,后者则以说唱的形式保留了嘲讽和调侃的权利。蚂蚱庙其实就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切片,如果说小说具有某种现代性,那就是这部作品所蕴涵的对于旧文化的批判精神。
乡野生活对于文学的意义
我喜欢和农村人交往,我的写作素材来自乡野阡陌之间。故事,人物,方言,甚至于我的创作情感,多半生发于乡野之间。我知道他们关心什么,他们也从我眼里看到了平等与友善。我曾自问,为什么对他们感到亲近?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生于乡村长于草野,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熟悉。乡下人在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思维路径诸多方面,我都知道一些,在那里容易找到归宿感。就连我的焦墨画,也带着浓厚的草野之气。

我并不特别喜欢底层,不仅不喜欢,还曾努力挣扎着摆脱出来。但是,秉持良心、不舍天性、幼稚天真的文学——这个化妆成美女的精灵——她喜欢,喜欢那里富有色彩的生活,喜欢那些鲜活独特的生命。底层是文学赖以生根开花的土壤,是文学纵横驰骋的山野,是文学想象的无垠天空。我爱文学,自愿以身相许,于是对其就有了超越自然主义的情感。因为这种情感,便想着去描述她,赞美她,既为她说好话,也自以为是地提及缺陷与恶习。底层并不都是美好,狭隘、愚昧、龌龊,比比皆是,虽然也能理解,到底难免痛心疾首。虽然种种,但我依然爱着这个容易被人忘记和鄙视的所谓底层。底层是文学的主食,不吃主食的人是不够健康的。他们不仅是社会的根基,也是文学的根基,没有对他们社会的充分认知,光靠几个上了彩釉的花盘,文学将是苍白的,文弱的,甚至是腐朽的。
底层社会拥有丰富的细节,而细节是小说的基本语言,这就让它有了更好的文学意义。《蚂蚱》描述的那个时代,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土地,牲畜,农具,每一粒粮食对他们都很重要,必得全力捍卫。那时的教育,除了识字,其他指导性目标都较弱,人的个性较少受教科书的影响。他们喜怒于形,不藏着掖着,听起来粗鲁而直接,但那就是底层语言的逻辑和质地。底层社会更多波希米亚风格,朴素,生动,原汁原味,新鲜而别致。这正是文学钟情的。
有人说,关心底层是一个作家的良心所在。这个话题,我其实说不清。是因为底层是大多数吗?好像不是。文学不像商品那样努力追求市场份额,所以没有理由非得关心不可。是因为在底层能够得到更多尊重吗?也不是。他们并不看重作家,他们看重的是能帮他们过上好日子的人。与文化人相比,他们更看重权力和金钱,看重互助和情谊,而非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底层人羡慕的其实是中层。如果攀比不上,就只能在同类中寻找微弱的差别以求慰藉,尽管是“席上滚到地上”,也有“仨钱不认俩钱的”现象。往人性深处探究文学,似乎可以这么说:底层是弱者,正常人有一种扶助弱者的善意,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作家眷顾底层,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我出身这个群体,但我清楚知道自己已不是这里的土著。和乡村大多数人相较,我的生活是不典型的,所以没有代表性。真正的深入,是从事底层某种职业,泥里水里,摸爬滚打,尝尽酸甜苦辣,看遍人情炎凉,然后才能写出真正属于底层的作品。如果狄更斯没当过伦敦的报童,《雾都孤儿》很难写得那么好。如果曹雪芹没经过“烈火烹油”到“眼看着你楼塌了”,纵有万种风情,也写不出红楼真相。“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破灶烧湿苇”“死灰吹不起”,非亲身经过那种生活,写不出那样的作品。

近二十年,我虽然住在乡村,毕竟不是农民,情感上和他们还是隔了一层皮。对于我,这里也有保持距离的好处。子夏说,虽小道,亦有可观之处,致远恐泥。我自知不能完全深入进去,也没有胆量和能力和底层打成一片,最好的姿态就是做一个旁观者。所以说创作小说,不单是因为身临其境或切身感受,更主要的是因为认知上的一点优势。
我基本属于传统价值观下的写作,同时又在当代文学观念中挣扎,一旦深入人性,便觉得山谷幽深,野兽凶猛。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文学所秉承的平民意识和正义感。正义感的本质是善和爱,是权利的平等和对个体的尊重。城市文明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有了认识乡村生活的一点优势,同时也促成了个人心路的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说,《蚂蚱》并非白捡,它是故乡特意为我准备的礼物,也是我对那片土地的回馈。
作者:王兆军
作者简介

王兆军,1947年出生于山东临沂,曾任《报告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散文集《皱纹里的声音》;长篇纪实文学《问故乡》及随笔集数部。作品《拂晓前的葬礼》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原野在呼唤》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把兄弟》获《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华语小说优秀奖。



农民日报社主办,中国农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2019- by farmer.com.cn.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