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是一个人的精神摇篮,每一个走出乡村的人,理应不忘乡村、善待乡村、敬畏乡村,乡村是来处,也是灵魂的归宿。


每个作家都有精神原乡,我的精神原乡是乡村。
乡村,是生长民族脊梁的地方,历数共和国典册中的英烈,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大都来自乡村。
乡村是一个人的精神摇篮,每一个走出乡村的人,理应不忘乡村、善待乡村、敬畏乡村,乡村是来处,也是灵魂的归宿。
乡村,是记忆里永不干涸的泉
乡村对于我来说,是总有汩汩清水外溢的泉,无论何时何地,那泉水总是甘甜清洌,浸润心脾。书写乡村,我的笔从没有生涩感,我知道是这清泉的作用,有清泉相伴,笔下的文字是流出来的。
我倾注心血的几部长篇都是乡村题材。比如《刀兵过》,是写辽河口绿苇红滩中一个叫九里的村庄。清末,这个芦苇滩上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接纳了一个流民之后,这便是后来九里的乡贤王克笙,王克笙父子的到来让九里有了主心骨。在乡贤父子的推动下,九里不仅没有被一茬接一茬的兵燹所吞噬,还生生不息地壮大起来,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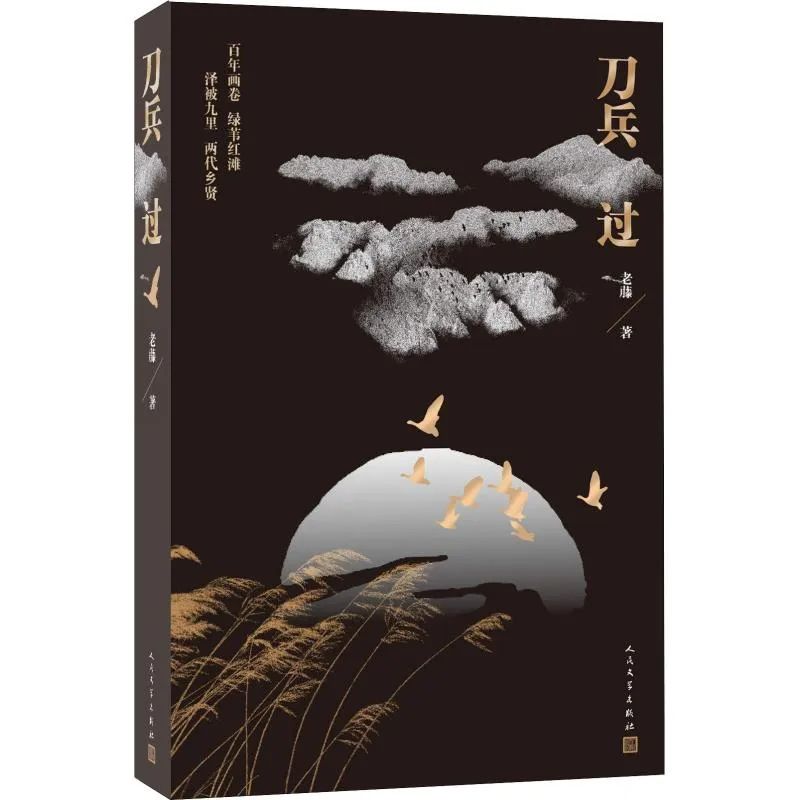
在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战国红》中,我写了一个叫柳城的乡村。因为有在辽西挂职扶贫的工作经历,我深知扶贫工作的难度和贫困农民的真实诉求,扶贫的关键是扶人,人扶不起来,投资再多的项目也不会持久。在这部作品中,我精心塑造了农村新人的形象——杏儿。杏儿是个身上有着新时代特征的女青年,在扶贫干部的培养帮助下,她成了柳城村村委会主任,柳城村因为有了年轻人,也就有了未来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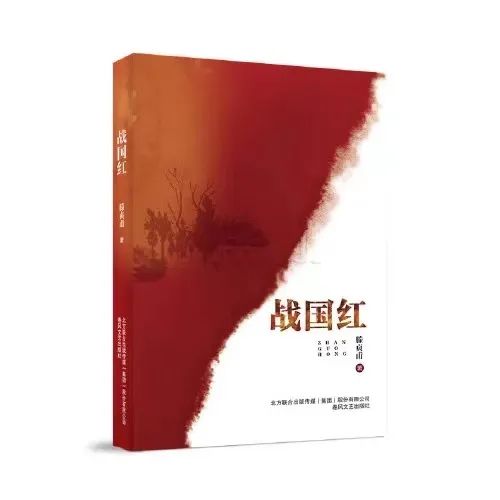
长篇小说《北地》则将众多乡村集中展现于一幅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画卷。书中的那些乡村都是北大荒腹地有着原生态韵味的村屯,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下属的嫩江、孙吴、逊克等市县,仍然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书中的村庄,比如那个湿地里长满湛蓝的钢笔水花的红花尔基,现在钢笔水花仍然是它特有的景观。如果没有北大荒乡村生活的亲历,钢笔水花这种情景是很难虚构的,这种花像是湿地里一簇簇蓝色的火焰,与蓝天白云形成了绝配。一般来说,红色的火焰在白天并不出色,也不会耀眼,当火焰以湛蓝色呈现出来的时候,那火焰仿佛就变成了精灵,能放大你所有的想象,钢笔水花所给你的就是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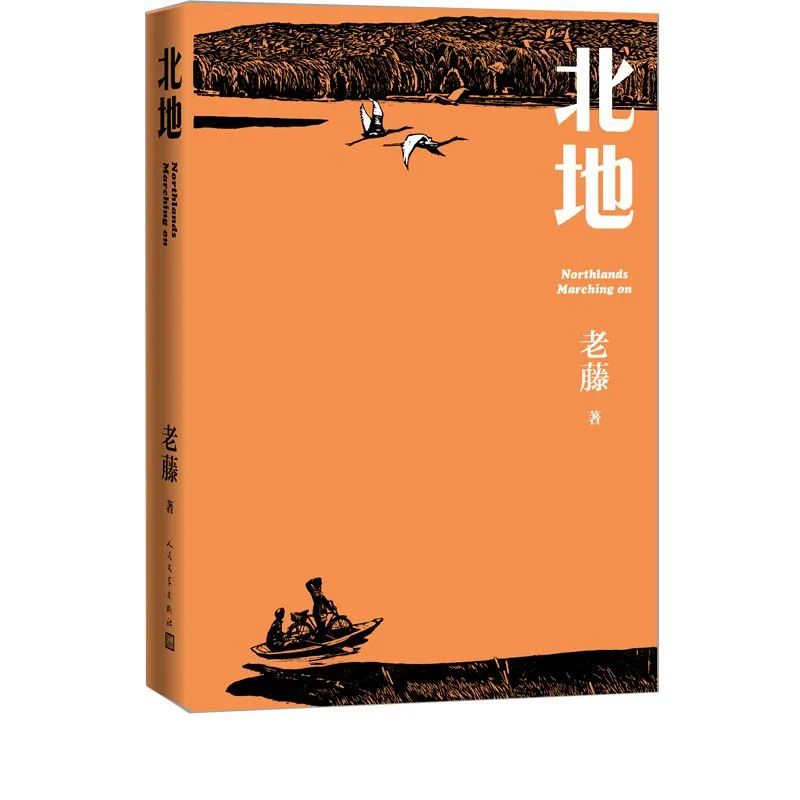
《北障》是一部关于北地的猎人笔记,在这部小说里我把小兴安岭深处的山村景致做了逼真描绘。我想,对那些没有北方山区生活体验的人,这种描述至少会有认知作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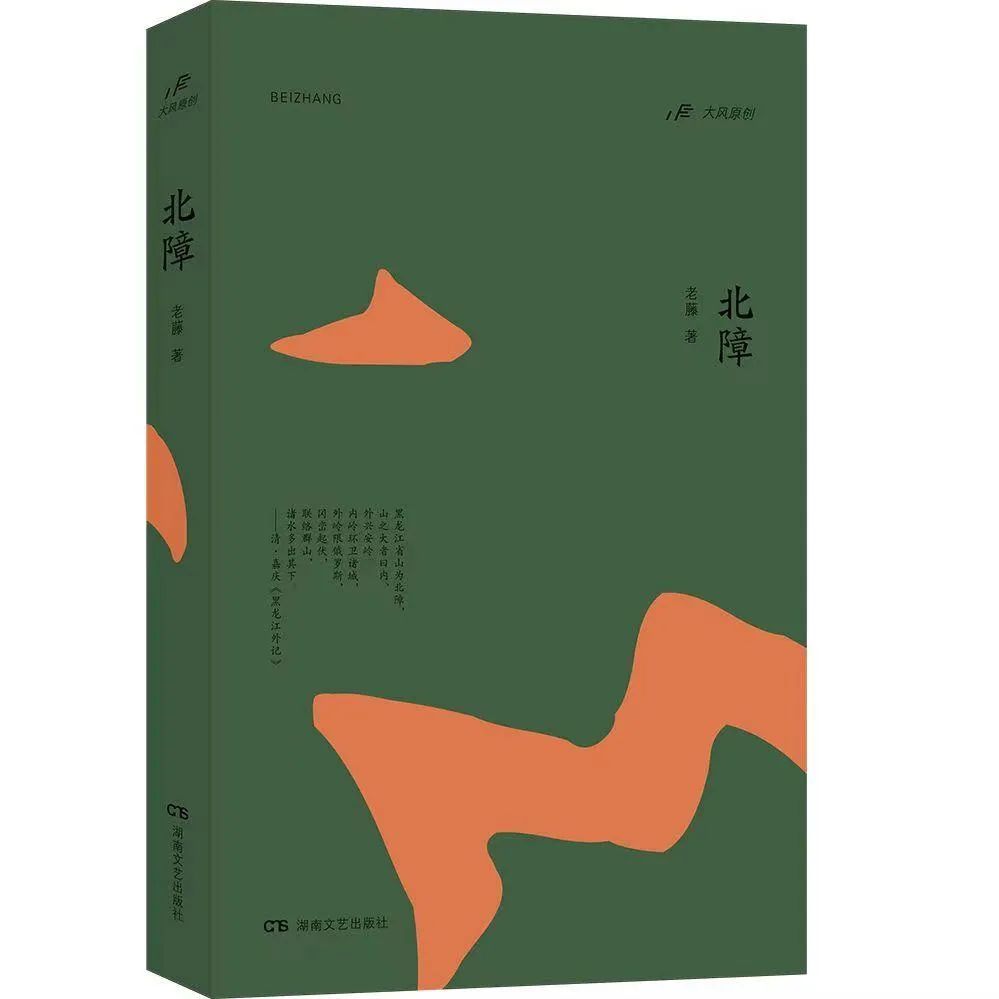
初春,落叶林还没有吐绿的时候,整个山区渐渐变成鞑子香的世界,那是一片片桃红色的花海。你不会觉得这是花,它就是一波波向你涌来的粉雾,在尚有寒意的春风里,这粉雾不用绿色装扮,是一种全裸的粉红,没有人会对此不动心。鞑子香在南方叫杜鹃,在朝鲜叫金达莱,在北障叫鞑子香,还是鞑子香这个名字棒,因为这个名字有北地特色。鞑子香开过之后,其他各种花才姗姗来迟地绽放,但后来者也可居上,有人们熟知的山丁子花、柳叶兰、鹿蹄草花、鸢尾花、野火球、狼毒花、刺玫,种类实在太多了。最美丽的是山丹、黄花和芍药,山丹是野百合,黄花是仙人菜,芍药的根叫白芍,是药材,但你不能挖,挖了就等于毁掉了一片和牡丹有一拼的芍药花。
夏季,北障仿佛被绿色的帷幔罩起来,满眼都是湿透的绿。绿色这种颜色很怪,干绿没什么看头,只有湿绿才有味道。这个时候,林间的草地是最美的,像一块块绿色的金丝绒,让人恨不得在上面打滚儿。各种蝴蝶是草地之魂,在野花中纷飞不止。运气好的话,会看到笨拙的旱獭站起来和你打招呼,它们前爪抱着食物,直立着身子四处张望,不时发出一声怪叫来吓人。与其他林区的猎手不同,这里的猎手很少打旱獭,旱獭的天敌是鹰和狐狸。北障人认为,旱獭是老天给鹰和狐狸准备的大餐,人不能与鹰和狐狸争食,世间万事万物各行其道,这个世界才会和谐。夏季,猎手一般不会打猎,但山还是要进的,主要是采集山货,比如木耳、蘑菇、猴头菇、桦树菇等等;采集各种浆果,比如一把抓、羊奶子、马林果、黑加仑;也采集五味子、刺五加、三七、黄芪等中草药;有时,也会拾些野鸡蛋、雁蛋。拾蛋是有说道的,必须拾没有孵过的蛋,孵过的蛋无论如何不能拾,拾回去也不能吃,倒害了一窝性命。那么怎么来区分呢?一般来说空敞着窝的蛋都没有问题,若是你走近之后飞禽再逃走的,那就不要拾了。夏季,北障最迷人的是草地与森林边缘的泡子,这些大大小小的泡子里有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白鹭、鸳鸯、野鸭、长脖老等,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个头像鹌鹑,却长着长长的喙,专吃小鱼小虾。泡子周围的灌木大都是榛窠和都柿窠,尤其是都柿,那是一种吃起来上瘾的浆果,比人工种植的蓝莓不知好上多少倍。都柿能天然防腐,可以长久保存,将成熟的都柿装入玻璃瓶中,拧紧瓶盖,放上一年半载依然酸甜可口。有巧妇用都柿酿酒,美味可口的都柿酒能让海量的汉子醉上一天一夜。都柿窠周围还有高粱果,这种酷似草莓的小果子不仅颜色红得发紫,而且味道极佳,一枚高粱果胜过一捧草莓。
进入初秋,北障就到了收获的季节,榛子等坚果成熟不说,红玛瑙粒一样的山丁子,带着雀斑的山里红,还有名字不雅的臭李子,到山里转上半天,回家不用吃饭了,各种水果、坚果早就填饱了肚子。深秋里,有时会在山中徒手抓住肚子胀鼓鼓的野猪或马鹿,它们因为偷吃了太多农田里的黄豆又喝了大量的水而腹胀难行,因此落入赶山人的手中。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秋季打场的时候农民会看住自己的牛,就是担心牛吃了太多的黄豆腹胀致死。如果因为贪吃搭上性命,说起来也难听。猎手们以此为戒,联想到狩猎切勿贪心,贪心必招灾祸。你走在草枯树黄的林地边缘,不时会有鹌鹑扑棱棱飞起来,鹌鹑飞不高也飞不远,猎犬会蹿起来力图叼住它,但猎犬不是山猫,没有成功的几率。猎手是不屑于打鹌鹑的,因为它的价值甚至不抵一粒子弹。
北障一落雪,猎手们狂欢的季节就到了,这个时候各种野兽都长满秋膘,个个体圆毛亮,等着猎手出征。北障是野生动物的天下,国家没有禁猎前,只要背枪进山,回来时便是满爬犁的收获,以野猪和狍子居多,运气好的还会打到黑瞎子和马鹿。冬季进山,你进入的是一个童话世界,这个神秘世界破解的密码就在雪地上,各种野兽会把自己的一切都涂写在雪地上。在猎手眼里雪地就像一块巨大的画板,各种野兽在画板上勾勒出自己的形态和行踪。猎手只要沿着足迹就不愁找不到它的藏身之处,除非那些蹲仓的黑熊,但即便黑熊蹲仓,也会在树洞入口留下哈气凝霜。
这便是迷人的北障,令人心驰神往的小兴安岭。
田庄,地瓜干堆起的记忆
我出生的村庄叫田庄,现在属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田横镇,那是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庄,在同治版的县志上,可以找到这个村庄的名字。我在田庄生活了八年,几十年了,每每想起田庄,我总嗅到一股香甜的味道,我感到童年的记忆是地瓜干堆起的,每一片地瓜干上都布满了糖霜。人的记忆大都与食物有关,或者说与食物有关的记忆往往更加深刻。我的童年是在咀嚼地瓜干里度过的,我喜欢吃熟地瓜晒出的地瓜干,那种甜香和筋道一直留在舌尖上。地瓜干虽然味美,但作为主食天天吃谁也受不了。那个年代,胶东人的主粮是地瓜干。每到秋天,全村男女老少都到田间地头,用擦板将新起的地瓜擦成地瓜片,就地晒干,然后作为口粮分给各家各户,人们称之为生地瓜干。应该说地瓜干是个好东西,不仅能充饥,而且还能酿酒,当时村民喝的酒主要是地瓜干酒。当然,对于胃口不好的人来说,地瓜干和高粱米一样,会磨砺你的胃,让你的胃酸过度分泌,我的好几位长辈,就是因为长期吃地瓜干患上了胃病。
我常常想,地瓜干虽然久食伤胃,但总比饿肚子要好得多。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是地瓜干保住了胶东人的性命,因为这个原因,我对田庄童年的记忆总是充满暖意。擦地瓜干是个很危险的活儿,常常有妇女不小心伤到了手掌,每每看到成筐成囤的地瓜干时,我总会想起村妇们缠着白纱布的右手。
关于粮食这个题材,作家们写了很多,但关于地瓜干的作品我还没有读到,我很为地瓜干鸣不平,也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地瓜干的小说,但几次提笔又不得不放下,因为地瓜干触及到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位,我总觉得还没准备好,不能糟蹋了这道带有糖霜的美食。
这便是迷人的北障,令人心驰神往的小兴安岭。
南甸子,我精神世界的彼岸
每个人心中都有彼岸,彼岸是一个人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从胶东迁到了黑龙江五大连池,那是松嫩平原上一个有火山的地方。我家居住的村庄南面有一条河,叫讷谟尔河,河水湍急,像一条巨蟒穿行在广袤的湿地里。放学后我常到河边去钓鱼,一根钓竿,一罐蚯蚓,一个柳编鱼篓,那是少年的乐趣所在。钓的是一种叫船丁子的冷水鱼,鱼不大,却坚挺,刺和肉都出奇地硬。因为水急,无法固定鱼漂,钓鱼时人会沿着河岸往下走,我们称之为钓走鱼。在没有鱼上钩的时候,我会把目光投向河南岸,南岸是一块细长的沙洲,沙洲外围长满河柳,中间高处则是成片的山丁子树,当然这是俗称,学名应该叫棠棣。听大人讲:沙洲再往南是连片的涝塘,里面长满一种叫小叶樟的苫房草,但因为过河危险,加之涝塘里有漂筏,很少有人过河去打草,也就没有人去打扰河那边的宁静。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五大连池风景。
河南岸的沙洲上有一窝水獭。这窝水獭有七八只,大大小小,应该是同一个家族。它们似乎无视北岸垂钓者的存在,在沙滩上打闹嬉戏,时而在岸上追来撵去,时而钻入水里,踩着水露出小脑袋仰泳。它们的眼睛圆鼓鼓的,像黑加仑,白色胡须很长,鼻翼能开能合,皮毛防水,出水后抖动几下便清清爽爽。因为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我对河那边充满了好奇,总觉得在那些茂密的柳丛和棠棣树林里还隐藏着其它大型动物。有一次,蒙蒙雾气里我分明看到一只白色的大型动物在沙滩上若隐若现,待雾气散去后又不见了。问河边一个种甜菜的生产队社员,这个年过五旬的社员说:“你有福气了孩子,河那边是白虎,能见到白虎的人会有好运气。”我知道这是糊弄小孩子的话,这块湿地里獐、狍、野鹿不少,而虎、豹这样的猛兽却闻所未闻。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工作,尽管无暇再回讷谟尔河垂钓,但记忆中河那边的情景仍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柳叶泛黄,棠棣醉紫,水獭一家无忧无虑、滑稽可笑的姿态仿佛还在眼前。后来,听说讷谟尔上游修了水库,那条湍急的河流变得细若游丝,有的地方旱季甚至会断流,裸露出干涸的河床,人们自然就可以跨过河去收割小叶樟,砍伐棠棣树,再将沙洲变成建筑采沙场,将涝塘开垦成稻田,那一家水獭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
我想,即使讷谟尔河还那么湍急,又能阻挡人类的紧逼吗?在《青山在》《萨满咒》《抬花轿》《黑画眉》等一系列生态小说中,我都表达了对“两山”理念的呼唤,因为我知道,乡村是“两山”理论的实践地,理论变为美好现实的可能性只能在乡村。
江山村,不仅仅是属于文学的乌托邦
江山村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这个村庄集中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乡村体验。在2023年第1期《长江文艺》发表的中篇小说《江山志》中,我对这个村庄有着详细的描述。
江山村得此名字皆因有江有山,江是白龙江,山是药泉山。白龙江是条被传说神化的江,如果归类的话,它属于嫩江支流,发源于著名的五大连池,蜿蜒流淌百余里,造就了六七块大大小小的沼泽后汇入了讷谟尔河。白龙江孕育了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传说,据说也正因这一传说才有了白龙江的名字。
药泉山是一座神奇的山,山不高,形状却奇特,像个巨大的玉箍立在原野上。药泉山的山瓮里有处毁弃的药王庙,后来胶东移民渐多,在药王庙旧址上建起了秃尾巴老李庙,简称老李庙,再后来,就演变成了钟灵寺。老李庙说是纪念秃尾巴老李,其实更是在固化某种乡愁,山东移民来到北大荒,需要一座老李庙来安放乡愁。以药泉山为中轴,往西便是排列有致的江山村。与江南民居不同,东北乡村的房屋大都规划整齐,从山顶西望,江山村就是一篇行间距等长等齐的文章,家家户户都有柞木杖子夹起的方形院落,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每家的柴垛都码放在院门旁,呈蘑菇型,这种垛法的好处是防雨,再大的雨水也耽误不了抱干柴烧火做饭。村中的红砖房皆用一种天蓝色的彩钢瓦,让排排房子看上去像兵营一般规矩。村子再往西是个小自然屯,这是闯关东老乡聚居的小西屯,它的存在,让江山村整体形状如同一个葫芦。
从药泉山北望,是一片茂密的白桦林,白桦林绵延数十里,像一道绿色的屏障阻挡着南下的北风。这片原始森林得以幸存,得益于森林三面尽是嶙峋的石塘,无路可行,即使采伐了木材也无法运出来。由此看来,想保护原始森林,最好的办法是不在森林中修路。原始森林中的路是动植物脖颈上的绞索,因为有路,人类就会蜂拥而入,动植物的天堂也就遭到了践踏,南美亚马逊雨林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白桦林是江山村村民采蘑菇、木耳和浆果的好去处,尤其难得的是,森林深处有一条泉水淙淙的飞龙沟,栖息着成群的飞龙。飞龙又叫岁贡鸟,是一种珍贵飞禽,属于上八珍之列。
药泉山东边,白龙江抛出一个大湾,形成了近千亩的稻田,因为是火山台地,厚度约尺半的腐殖土层下有一层坚硬的火山岩,岩下布满四通八达的地下河。挥镰收割的季节,会听到地下有哗哗的流水声,稻田由此得名响水稻,与著名的响水大米齐名。千亩稻田是江山村八百户人家的口粮田,面积虽不大,但产量不低,米价也好。稻田再往东,便是一块叫欢欣岭的坡地,村民在这里种植土豆。江山村的土豆皆为红皮,淀粉含量高,适合漏粉,因此成就了著名的小惠红粉坊。六七月份,白色和紫色的土豆花开满欢欣岭,欢欣岭如披上盛装一样迷人。很多人没有在意过土豆花,其实,土豆花自成花束,是一种非常优雅的五瓣花,橘黄色的花蕊结结实实,拱卫着一株绿色的花萼,内敛而不张扬,朴实而亲切。翻过欢欣岭,是一个宁静的湖泊,湖水呈海蓝色,因常有丹顶鹤栖息,当地人称之为鹤鸣湖。鹤鸣湖中生长一种叫噘嘴岛子,白鱼,镰刀型,细鳞,肉质鲜美,是美食家的最爱。鹤鸣湖湖底无沙,皆是一种类似于紫砂的火山泥,泥软而不黏,踩上去特别柔滑,泥中生长着一种大型河蚌,个个都有两三斤,但少有人采食,适合养殖北珠。
药泉山的南面有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湿地里有许多泡子。泡子里都有花样繁多的淡水鱼,以鲫瓜子、湖罗子、柳根儿、老头鱼和鲶鱼居多。因为鱼多,便引来了长脖老、苍鹭等大型水禽,偶尔也有天鹅栖息。奇怪的是大雁不在这里停留,大雁落脚多在无水的草地和林地边缘,当地人的说法是大雁义气,不与水禽争领地。泡子之间相对凸起的地方,则长满高低错落的山丁子树。春天,一树树白花戴云披雪,让人想起最美人间四月天的诗句;秋天,满树红盈盈的山丁子如串串朱玉,又像满枝玛瑙,映衬在池塘中,让一幅幅倒影成了美图。
其实,这个描述不是虚构,那是我青年时代真实生活过的乡村,我想以文学的方式让乡村美景得以永生。
服务邮箱:agricn@126.com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4395205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354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170078 京ICP证05068373号
农民日报社主办,中国农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2019-2025 by farmer.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