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去世很多年了,至今让我无法忘却,
常常想起的是那一次父亲的眼神,
还有那一次父亲的号哭和愤怒。
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一
父亲出生在农村。在我的记忆中,爷爷脾气耿直,不喜欢大脚的奶奶。所以一辈子就生了父亲一个儿子,父亲是地地道道的独子。
父亲考上的是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西安解放后,也任职于西北工学院。父亲当时是西北工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三十出头。父亲教授土木建筑专业,据父亲说,他的课程那时候非常受欢迎,每逢他讲课时,大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当当,有时候连过道上都站满了学生。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十分偶然。
父亲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板,长长的脸,高高的鼻梁,天庭饱满,额头很宽。我爱人曾经多次说我父亲不算帅,但一看就很有派头。派头,就是有气质的意思。
我爱人的看法应该准确,所以父亲在大学时,不乏喜欢他的女孩子。最终确定关系的是一个同年级的女同学,如果当时他们成婚结为夫妻,铁定也就没有我了。
1944年左右,那时西北工学院遭到最猛烈的一次日本飞机的轰炸,学院死伤多人,其中就有父亲当时已经确定对象关系的那个女同学。
父亲极少说过他与这个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无从了解这个女同学的家庭情况和性格长相。但今天看,正是因为父亲这个对象的被炸身亡,才彻底改变了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一直到大学毕业,父亲都没有再找对象。
大学毕业不久,日本投降,此后国共谈判破裂,终于兵戎相见。
为了避险,父亲去了甘肃天水中学教书。父亲在天水一共待了四年,一直到1949年5月咸阳、西安解放,已经迁址西安的西北工学院通知父亲回校任教。所以建国后父亲的履历表上,工作时间是1949年5月,属于离休。
父亲大学毕业时回了一趟老家。那时候的父亲已经二十六岁了,在当时属于超大龄青年。家里的爷爷奶奶自然急得抓狂,就在村里给父亲找了一个,也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属虎,比父亲小五岁,已经二十岁了,因为是大脚,所以一直找不到对象。母亲的大脚,是姥姥心疼娇惯的结果。那时候已经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新政府开始禁止缠脚。但在偏远的乡村里,缠脚还是父母对女孩子不可更改的硬规矩。女孩子不缠脚,属于离经叛道。所以好多家庭里,私下都仍然逼着女孩子缠脚。姥姥对母亲的放纵和疼爱,让母亲的每一次缠脚,都遭到顽强的抗争和逃匿,久而久之,对母亲的缠脚也就不再逼迫不再过问。当然,不缠脚的恶果和结局就是村里家境好点的人家,没人愿意娶一个不缠脚的女孩子做媳妇。母亲一直到十九岁了,还是极少有人提亲,只要说是大脚,便立刻无人过问。那时候的女孩子十四五岁都已成婚,而将近二十岁的母亲仍是孑然一身。
面对已经过了十九岁的母亲,姥姥已经十分绝望,曾多次谋算着把母亲嫁给一个二婚或者家境很差的老光棍。
这一切大概都是天意,父亲那年回来时,有人撮合,见到了十九岁的母亲,父亲欣然同意,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月后,就和母亲结了婚。
父亲曾多次给我说过,如果母亲是个小脚,他那时绝对不会在老家与母亲成婚。
所谓的缘分,就是母亲的大脚,和父亲的文化背景,让他们一见钟情,终成眷属。
一双大脚,让母亲无法成为村妇;还是这双大脚,让母亲成了教授的夫人。
也许正是这种命运的安排,让母亲一生不离不弃,跟随了父亲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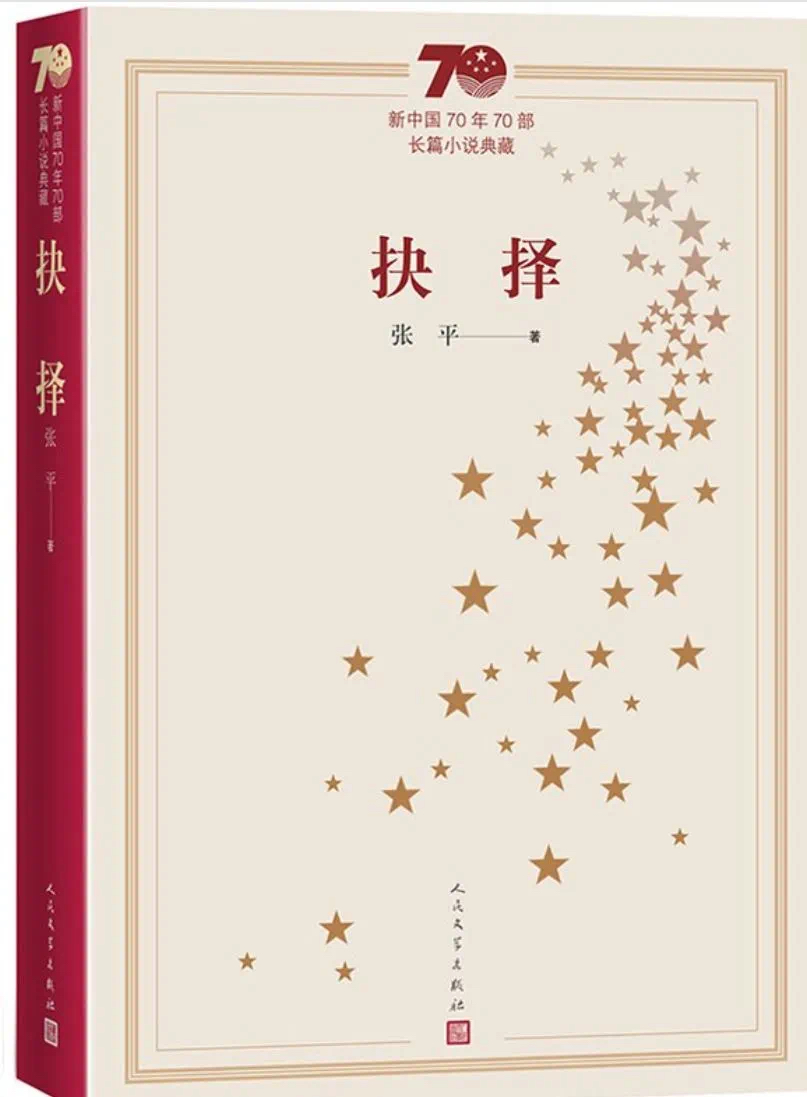
二
当时(父亲出事时)我还很小,无忧无虑,天真烂漫,一家中唯一的男孩,对当时事态的严重性,对家庭的剧变,可以说一无所知,毫无感觉。
我唯一记得的情景是,那一天与母亲一起洗脸,当母亲给我擦了脸,我抬起头来时,看见母亲也在用毛巾擦脸。刚开始以为母亲是在擦脸上的水珠,但看到后来,才看清母亲是在擦眼泪,一把擦下去,泪水立刻又汹涌而出,再擦一把,泪水再次汹涌而出。母亲静静地蹲在脸盆旁,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声息,就那样默默地擦了一把又一把,怎么擦也擦不完。
由于母亲当时没有工作,父亲的出事,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彻底的垮塌和最终的去向。三十二岁的母亲只能离开西安,举家遣返回到老家山西新绛县的一个偏远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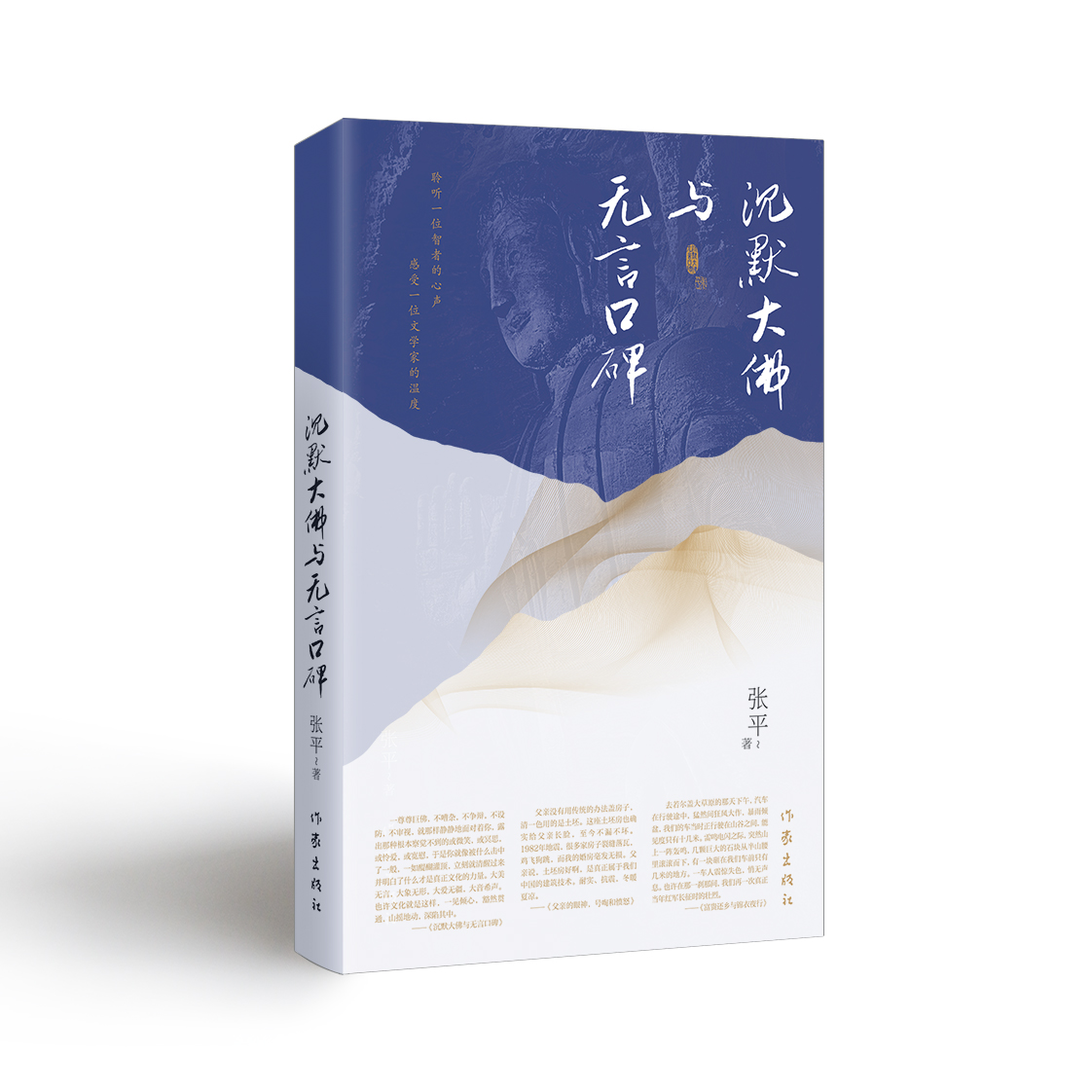
一直等到1962年初父亲回到老家时,我才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父亲。
父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在学校上学。放学回到家里时,奶奶告诉我,你爹回来了。
父亲脸面黑黝黝的,连脖子也是黑的,一点儿也不像个大知识分子,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父亲那个在任何时候都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大背头。
从父亲离开,到父亲回来,我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村娃。那时候的衣服没有化纤产品,洗一遍就成了灰乎乎的,穿几个月就变得破破烂烂,尤其是布鞋,不到一个月就穿得前后都是窟窿,大半截脚丫子都露在外面。即使是冬天也是这样,穿棉衣没有内裤内衣,连袜子也穿不起。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样子一定让父亲感到辛酸内疚,加上自己的学习一直很好,所以父亲连呵斥都没有呵斥过我一次。
我的学习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一些基因,从没记得下过什么功夫,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我的作文一直是范文,在班里被老师念了又念,不断传阅。
我考初中时,成绩全公社排名第二,全县排名第五。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你的成绩其实应该是第一,语文数学都没有错题,扣分原因主要是卷面太潦草。其实父亲和老师都知道,不是什么卷面潦草,而是钢笔太差。我用了两年的钢笔是父亲带回来的一支旧笔,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墨水灌多了漏水,墨水灌少了不出水。笔尖已经成了平的,劲用大了洇一片,劲用小了又看不清。那时候的钢笔,一支一块多钱,对父亲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上初中时,连住宿费、伙食费、学杂费每个月需要八块钱,这真正是一笔巨款。父亲一到了月头,就对我的这八块钱发愁,除了变卖家里的东西,其余就是借钱。上了几个月,父亲和母亲商量了好多次,准备让我休学,因为家里每个月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没过多久,学校突然间全部停课了。再后来,我就在村里彻底务农了。
只有真正在村里生产队劳动时,我才意识到了父亲的艰辛和不易。
父亲是一个几乎没有在农村劳动过的知识分子。父亲六岁上学,十岁时就到了县城上完小学,此后几乎再没有回过农村。因为战乱,即使是节假日,也很少回来。
政府曾给了父亲一份工作,让他在一个建筑公司做杂工,一个月四十五块钱左右,但这份工作被父亲拒绝了。
在几年的时间里,父亲学会了犁地、耙地、锄地、耕地等所有最基本的农活。父亲的肩膀左高右低,几乎有三四厘米的落差,只有我清楚,这是因为父亲挑担子不会换肩所造成的结果。
当然父亲也有不会干的农活,比如赶车,比如播种,比如割麦子,比如种菜种瓜……还有,父亲一直没有学会做饭,连起码的擀面条、炒菜也不会。
事实上父亲是一个乐天派,有时候偶尔说起在农场的生活,总是满脸笑意,以一种赞叹的口吻叙述当年的一些往事。到了田间地头,父亲的语言天分就会得到尽情的发挥。每当干活休息时,父亲的身旁总会围满了人,听父亲绘声绘色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和章回话本。父亲总是恰到好处地讲到关键处,戛然而止,让大家且听下回分解。

三
父亲最得意的建筑,就是给我修建的那所婚房。
订婚的那年我已经二十四岁,已经从稷山师范学校毕业,在县里的东街小学当了教师了。只是工资非常少,实习工资一个月二十五块五。
订了婚,最晚也得在第二年结婚。当时什么也准备齐全了,就是缺了一项,没有可以结婚住的房子。
这是个天大的事情,农村人常说,娶媳妇盖厦,经过的害怕。那时候正是家里最拮据的时候,尽管已经不怎么缺吃少穿了,但要拿出钱盖房子,那几乎是天方夜谭。没有婚房,儿子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娶媳妇的。
今天我才体会得到,那一年,对父亲来说,是他一生的一次大考。他得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那时候盖房子,再便宜也得两三千元,这样一笔巨款,父亲是无论如何也筹不到的。再加上当时的婚俗,订婚也得有一笔不菲的礼金。那时自己的情况也很差,借个一百二百也不是不可以,但你想在那个时候找人借几百元上千元,门儿都没有。何况因为在县城上班,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还欠着一屁股债。我那时候甚至都做好了另一番准备,实在不行,结婚时就暂借同学的房子住几个月。
但父亲有父亲的想法,他堂堂一个男子汉,就这么一个儿子,绝不让儿子在结婚时,借别人家的房子当婚房。
今天我也没想明白,父亲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了自己的一套计划。他要亲自设计,亲自修建,要给他的儿子建一套结婚新房。
那时候我在县城学校教书,除了偶尔回家,平时都在学校里待着,直到有一天,母亲捎回话来,让我星期天回来一趟,赶上一头牛,到北山下,在汾河边的大坡下面去接父亲。
回到家才知道,父亲到北山拉木材去了。
北山属于吕梁山脉,是能在老家的山坡上看得到的远远的一座座蓝色的大山。
我曾在北山上拉过煤,一人一辆架子车,一来回一个星期,去三天回四天,一架子车煤可以装到一千多斤。一千多斤煤,一个家差不多可以烧一冬天。最重要的是,便宜,直接到煤窑口去拉煤,比在市面上买煤要便宜一半还多。
拉煤车从北山下来,过了汾河,就是一路高坡,大约四十里路,就回到了家里。每次拉煤,都是父亲牵着一头牛来接我,每次见到父亲时,便会松一口气,这回总算安全到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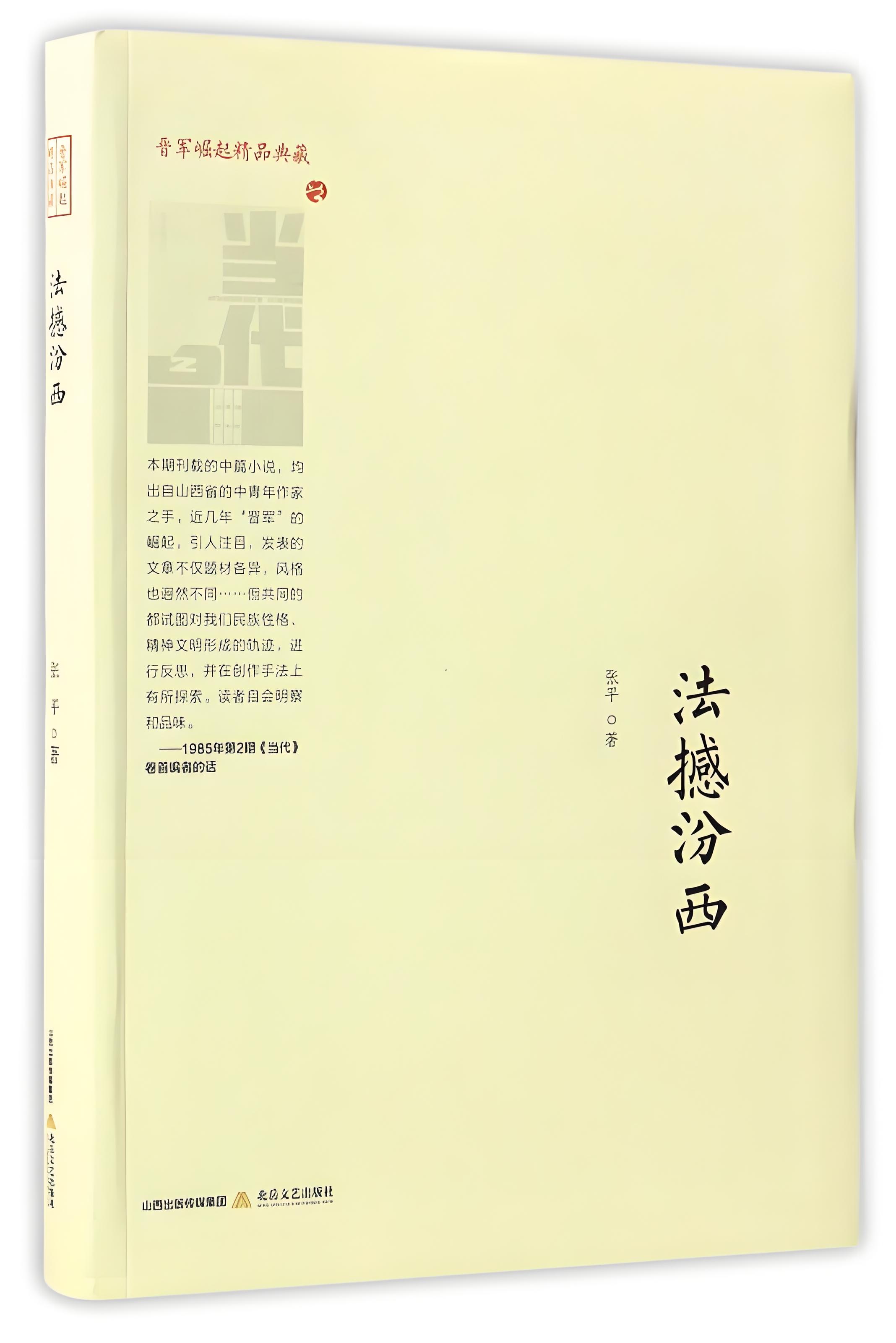
但这次不同,母亲是要我去接父亲。那一年,父亲已经快六十岁了。当我在坡底下第一眼看到父亲的影子时,眼泪止不住地就涌了出来。
父亲拉着满满的一车木材,有两个父亲那么高,足有三四米长,八九百斤。
正是大热天,父亲穿着一个百孔千疮的背心,几乎光着膀子,浑身晒得乌黑。父亲的大背头,在风中十分凌乱而又稀疏。灰白拉碴的胡子,几天没刮了,稀稀拉拉地在黝黑的脸上显得十分醒目。
我突然感觉到,父亲原来这么瘦,又这么老了。
就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父亲,一个干巴瘦的父亲,一个六十岁的父亲,要给儿子亲手建造一座婚房。
也许就是几十秒钟,我用极快的速度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不想让父亲看到我的眼泪。
其实那次父亲拉回来的木材,充其量也就是拉回来一车山木棍子。两百多根,大都是山中的荆棘秆儿,细的直径有两三厘米,粗的也就和玉茭秆差不多。
一架子车木材,父亲总共只花了七十多块钱。但父亲信心十足,说这样的木料给房子做椽绝对没有问题,既有硬度,又有韧性,像钢筋一样,拉力超强。父亲说他前后已经在山里跑过几次了,这都是在村里挨家挨户收来的。山上有长得好的木材,但村里管得严,不让采伐。这些能收到的山木,已经算是非常好的木材了。
听到父亲的话,我立刻又意识到,这座房子只能靠我们父子俩打拼了。父亲出主意,我出力。等前期建房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真正盖房的时候,再找亲戚邻居帮忙。
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打了两千多块土坯。用这两千多块土坯,和父亲从北山打回来的木材,前前后后用了二十多天,总共花了二百七十多块钱,终于建成了我的婚房。
父亲没有用传统的办法盖房子,清一色用的是土坯。
这座土坯房也确实给父亲长脸,1982年地震,很多家房子裂缝落瓦,鸡飞狗跳,而我的婚房毫发无损。
父亲说,土坯房好啊,是真正属于我们中国的建筑技术。耐实、抗震,冬暖夏凉。
打土坯在我们那一带,叫打胡墼。父亲要盖的房子,肯定是用不起砖的,一块砖那时候得七八分钱,一间砖房,至少也得用万把块。爸爸设计的婚房是小两间,怎么也得一万多块砖,那差不多就是一千多块钱,这还不算别的开销,所以肯定是用不起的。其实我很清楚,我的婚房只能是土坯房。
四
父亲吃饭从来不挑剔,母亲做下什么就吃什么。
后来有一次,从父亲的眼神里,我感觉到了父亲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那一天,有个队里的年轻人,端着半碗炒菜,上面叠着两张饼子,一边嚷嚷,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饼子。
这本是十分平常的情景,就算有些家庭条件好的人能吃得起白面大米,在人面上也没人会当回事。大家瞟一眼也就得了,没人会表现出什么异样的表情。
但那次不同,当我随意瞄了一眼父亲时,一下子让我看呆在那里。
父亲两眼直勾勾地盯在那个人的碗里,分明现出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一边一眼不松地看着,一边时不时地吞咽着口水。
很长很长时间,父亲都那样旁若无人地看着,似乎完全进入了一种无我迷离的状态。
我当时恨不得一头钻到地缝里去,父亲的样子实在太丢人了,太让人难堪了。
一直到今天,一想起父亲当时的那种眼神,心里就一阵阵揪心般的疼痛。
父亲那天一定是太饿了,也一定是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这种白面饼子了。
父亲曾经给我说过一件他亲眼看到的事,他当年在农场干活时,有位母亲带着吃的千里迢迢来看望儿子,儿子当着母亲的面,一口气吃了七个饼子,一斤红糖,随后喝了一碗水,一口气没上来,当时就憋晕在了那里,再也没有醒过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在父亲的记忆里,白面饼子应该是父亲永远无法忘却的美食。
从我记事起,我几乎没见到父亲哭过,甚至都没有见到过父亲掉眼泪。那年奶奶去世时,可能由于忙着奶奶的丧事,每天焦头烂额,也没有见父亲哭过一声。
母亲也说过,你爸眼硬,轻易不掉眼泪。
那一年我的小说获了奖,还有两部小说被改成了影视剧,父亲专门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示祝贺。父亲的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儿子,你就像一匹野生野长的小马,独自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给自己闯出了一条长满鲜花的道路……”父亲在信里还给我说了家里的一些情况,父亲刚正的字体和欢快的语句,显示着父亲的满意和快乐。我也很快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让他和母亲多多保重,家里还有二亩地,年龄大了,能干就干点,不能干就别干了。
春节回家时,有一天,母亲悄悄对我说,你上次在信里写啥了,让你爸哭了一晚上。我听了不禁大吃一惊,有些发怔地看着母亲:“我爸哭了一晚上?”
母亲说,那天晚上真把她吓着了,连邻居也跑了过来,怎么劝也劝不住。父亲哭得昏天黑地,像天塌了一样,一声接一声地放声大哭,先是在屋子里哭,又坐到院子里哭,晚上睡下了,仍然一阵子一阵子地哭。哭到了第二天,眼睛都肿了,连饭都没怎么吃。
我愣了好半天,问母亲是哪封信啊,我不记得在信里说过什么不好听的话,真的想不起来了。
母亲把那封信给了我,我看了一眼,就是父亲祝贺我时,我给父亲的那封回信。看到这封信,我也立刻明白父亲为什么会那样号啕大哭了。
我在给父亲的那封回信里,写了这样几句话:“……一切都好起来了,但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会想到爷爷,想起奶奶。眼前时不时会浮现出精神失常的爷爷光着身子在满街跑的情景。有时候在睡梦里,也会突然醒来,看到寒冬腊月,奶奶一边为我暖被子,一边冻得哆哆嗦嗦的样子。让我一直难受的是,奶奶去世时,疼痛难忍,能喝的药只有正痛片……”
可能就是这一段话,戳到了父亲内心深处掩饰了很久的伤口,让父亲椎心泣血,痛不欲生。
那时候,父亲住的新房已经建了起来,父亲的工资,因为是离休,也是当时同事里面最高的。改革开放,让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孩子们也算争气,让他终于能在人们面前挺起腰杆来。也许这是晚年的父亲一生中最惬意、最知足的时期。
但总有一些让他无法释怀的情结,地久天长地缠绕在他的心底。
也许就是这封信,让父亲憋屈了一辈子,如江海波涛一般的长怨深悔,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点,撕心裂肺,死去活来,放声号啕,大哭了一场。为他的父亲,为他的母亲,也为他的过去。
我常常想,也许平时看到的父亲,并不是那个真实的父亲。真实的父亲,一直隐藏得很深很深。
父亲快七十岁的那一年,我大姐的儿子在山大上学,没有专心学业,悄悄一个人回到了我们家,他的事父亲自然也是知道的。当时正是吃饭的时候,父亲不依不饶,一边追一边骂:“刚八的,什么东西,毛头小子你懂什么!反了你了!”
父亲从不骂人,连大姐也算上,也是第一次听到父亲这样骂人,至于“刚八的”是什么意思,我今天也没有闹清楚,大概就是王八蛋一类的意思。父亲不可遏制的愤慨和怒斥,也许是因为觉得他一生最好的岁月,就是眼前的改革开放时代,他无法容忍任何人对这个时代的任何亵渎和毁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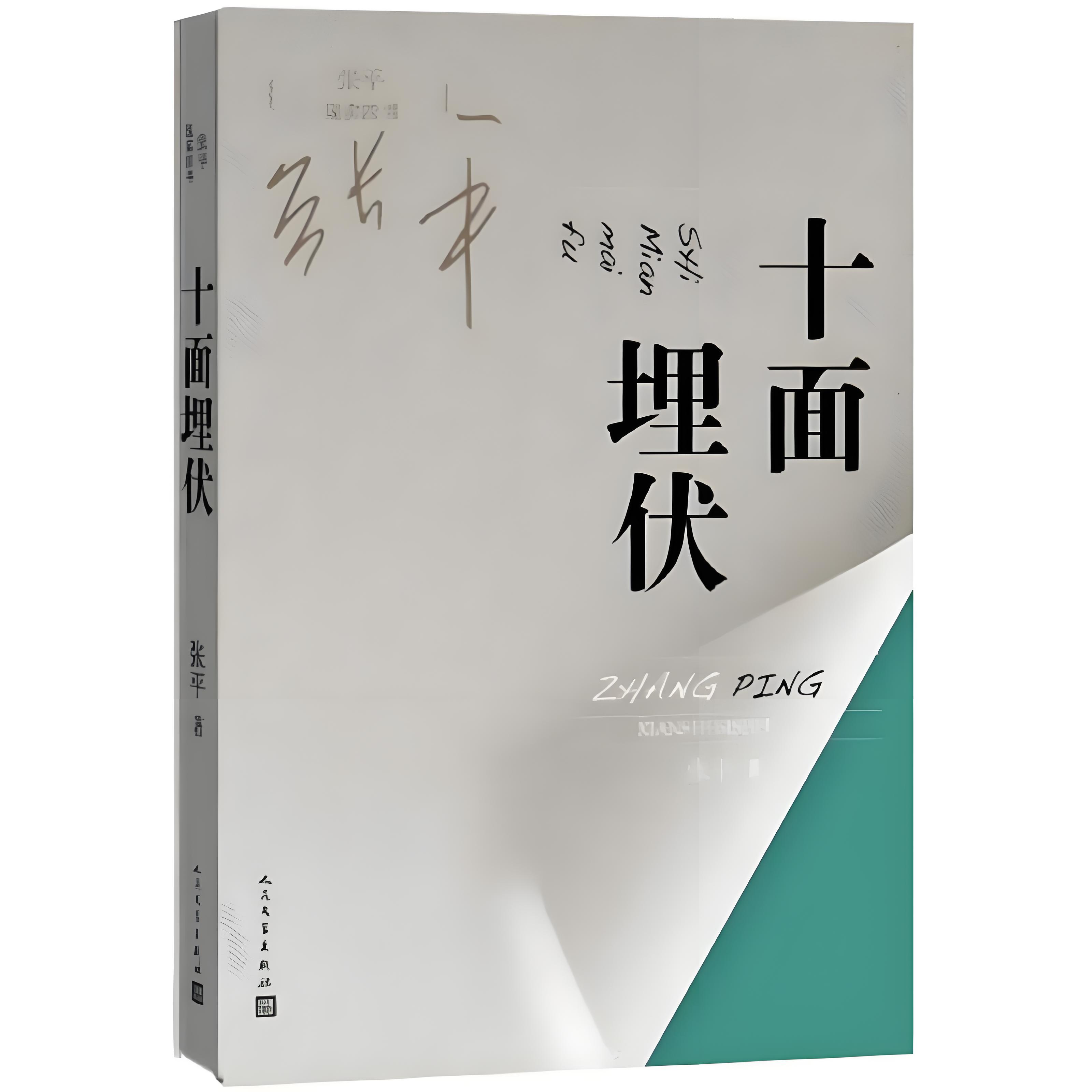
掐指一算,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父亲早已安息,母亲也已经陪他长眠。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里,在无数次睡梦中,父亲微笑,欢快,乐观,幽默,沉思,愁苦,郁闷,无奈,绝望,消瘦,劳顿,倔强,高傲,衣衫褴褛,颤颤巍巍,满头大汗,四处奔波,忙忙碌碌,疲惫不堪的形象仍会凸显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似在眼前,朦朦胧胧,又很远很远。
作者:张平
作者简介:

张平,1954年生,山西籍,生于西安。历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主要作品有《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其创作成就卓著,曾获茅盾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项,并八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抉择》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入选“建国50周年献礼作品”及“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服务邮箱:agricn@126.com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4395205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354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170078 京ICP证05068373号
农民日报社主办,中国农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2019-2025 by farmer.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