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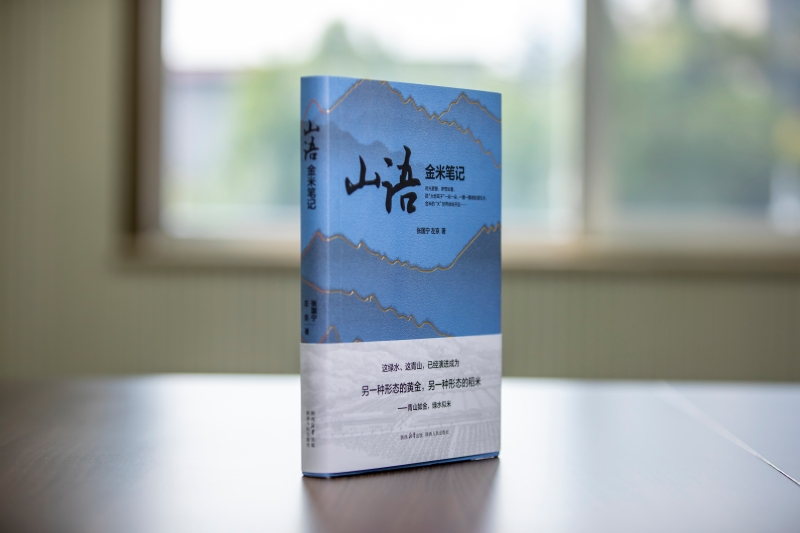
一
从进入金米村的那一刻起,我便不断试图寻求“介入”的逻辑起点。我无法把它简单地解释为一项采写任务,即便金米村因为名气之大,的确正吸引着包括我在内的媒体大军源源不断赶来。
我要完成的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这种写作形式自诞生之初,便自带文学与新闻跨学科交叉的特质,强调通过作者的“个人体验”,尽最大努力挖掘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在那样的“现场”和“故事”中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是个体性和公共性的有机综合,而作者“个人体验”的质量无疑成为影响作品“真实”的核心变量。
刚到金米村不久,我便被村支书李正森邀请加入南下浙江余村“取经”的队伍。一个陌生面孔的记者与村“两委”干部窝在一辆七座车里,共同闯过六安疫情风波,在80个小时里奔行3500公里,学习满载而归时对着大雨滂沱的黑夜引吭高歌,透露着各自说出来的和说不出来的关于这座村庄的理想。
随着不断深入村庄的社会生活内部,我将“外来户”正森当选村支书、驻村干部“小李子”在临别之际收到帮扶户送的干牛粪、东北木耳技术员咸嫂子被68岁的定富老汉拜师等一连串事件拼接起来,惊奇发现在若干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有它必然发生的逻辑:
当地开放包容的“移民文化”和金米村上下一致求发展的决心,犹如社川河河床底部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能量,蓄势待发,终于引发乡土社会机体组织内部的强烈震动——以血缘和地缘亲疏形成的“差序格局”逐渐被打破,乡村政治摆脱了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一切有利于激活村庄生命力的外来力量被拥入怀中,打开了乡村振兴新的视野和希望。
诚如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因此,作家梁鸿反思十多年的非虚构写作经历:“个人经验”和“知识体系”不是你写作的依据和确定自己的支撑,而是需要不断克服的对象。
我不能否认我的“个人经验”和“知识体系”必然在其中发挥作用,至少正是因为我从外来人的视角才会一路捕捉到这里。但与此同时,和村庄里的人近乎亲人般真诚的相处,奠定了我顺利获取第一手素材的基础,从而得以不断修正和扩充自我认知,以图无限接近着探寻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渊源和行为方式根本的目标。
二
及至坐下来摆开架势开始写作,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当“我”已身处其中,与故事里的人和事发生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交集,那么该如何恰如其分处理对于村庄的情感?
驻村采访结束的前一晚,村里人跟我说:“你就是我们金米人么,走啥走,明天看我们在村口挡你。”这句话让我一瞬间想起当年我出嫁的时候,老家满村的树上绑满红毛线,那千丝万缕仿佛都在诉说不舍。
“作者不敢擅用自己的权力,必须盘察并惊醒自身的一切,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理智和感情,和自我博弈,最终和‘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形成对话。”作为后来者,我几乎经历着和“梁庄三部曲”的作者梁鸿一样的心路历程。
我甚至一度企图杀死“我”,以便和故事里的每个人划清界限,来证明他们的悲喜客观存在,避免被质疑沉溺个人情绪而损害到作品“公共性”的部分,那才是作品想要表达的重点。而我也无须因对于一个并非自己故乡的村庄表现得过于亲昵而担心遭受质疑,即便这种情感的建立源于你来我往的朝夕相处而产生的信任和认可——但那显然已经是故事之外的故事。
本以为摆脱了“我”的情感羁绊,写作会变得顺畅,但真实的情况事与愿违。原本有“我”参与其中的事件因无法还原现场全貌,讲述显得费尽心机却仍然支离破碎;由“我”主动为之而设置的议题没有了起始的缘由,故事难以引人入胜;而那些正在发生的被“我”观察到的种种耐人寻味的生活细节,脱离了“我”的口吻,文字是那样索然无趣,平淡乏味。
写作被迫中断。我冒着一阵阵冷汗,在电脑屏幕上打下一段文字,然后又将它一字不落地删掉,身心备受煎熬。直到教师节来临的前一天,我回到了金米村。
三
回来是因为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黄龙山小学复校。
这件事在我离开之前已经埋下伏笔,甚至于它的起因便是受金米村干部所托,我和从北京回乡探亲的江峰跑了趟柞水县教育局,就目前乡村教育的问题跟当地干部做了一番探讨。
我竭尽全力使自己保持中立客观。如若去掉情感的砝码,天平的两端,“撤校”或是“复校”哪个利大、哪个弊大?我的答案是:不知道。
从政府的角度看,复校所要付出的既有“显性成本”,又有“隐性成本”;从村民的角度出发,账本上算的是“撤校”后单个家庭因陪读而额外支出的各种花销;从村干部的角度看又不同,因“撤校”所引发的劳动力外流、离婚率走高、家庭养老缺失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乡村振兴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我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勒令我,绝不能干预事件进展。直到复校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地,我回到金米,听正森他们讲述在这期间所做的努力与经受的磨难,亲眼看到一所已经停办了一年的小学“起死回生”,我想起来有次村上开会,播放过一个纪念袁隆平院士的短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团队必须有一个核心领军人物,这个人要坚韧、百折不挠,才可能带领他的团队冲破一次又一次的关隘。
我不知道多年以后,当我在黄龙山小学见到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会如何回忆金米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会不会他们中也有人被一群未来的孩子围着,坐在村口那棵老核桃树下讲故事,感念今天父辈们的坚韧与坚持、奋争与奋发,改变着村庄和个人的命运。
返程途中,我的眼泪擦干了又流下来,反复在心里默念,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作者:张国宁 左京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和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梁鸿:《非虚构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体间性》。



农民日报社主办,中国农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2019- by farmer.com.cn.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