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有一天,他们会自觉地爱故乡,
自觉地建设故乡。
他们在外闯荡的经历经验,
对未来建设家乡必定有极大帮助。
蛇年春节,我决定元宵节前一天或者元宵节当天再回村,以躲避没完没了的应酬和吃吃喝喝。通常情况,初七到初十,村里在外工作、务工的人员离村,回到各自讨生活的城市,三百来人的村庄安静下来。我好静,不太喜欢数桌人挤在堂屋里的那种热闹。说到底,我已经不能完全融入村里人的生活,他们的快乐、欢声撞不开我潜意识里关闭的心门。村里春节的喧闹,有童年的召唤,我向往;有少年贫困的创伤,我逃避。
过了初十,见我还没回村,父亲着急,来电话催我们兄弟四人回村请客,不然,客人全都离村,大过年的,连餐饭都捞不着。陆续给父亲拜年的大都是村里的晚辈,每来一个招呼一餐,太烦琐,不如攒着,统一请客,摆个三四桌,热热闹闹。
往年初七前,如果我们在外的四个兄弟没回,小弟便承担主持请客的任务。小弟当年在县卫校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回村里当大队干部。当干部有权有补贴,不知道小弟看中的是权力还是害怕学医的难度,反正没人劝得住,“逃学”回了家。他卸任大队干部后,外出务工数年,然后回村扎根。小弟成为极少数留守村里的中年人之一。他代表父亲主持请客次数太多,我们四个当哥的过意不去。虽是过意不去,却少行动,包括今年还想赖掉。父亲来电,使我个人的“阴谋”破产。
今年春节,我想逃避的饭局,一餐没少。我不禁自我调侃道,人算不如天算。
 光盘
光盘
一
我们那个叫栗树脚的小山村,位于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东山瑶族乡,四面环山,全村有“盘孟王唐”四姓。我记事时就不见唐姓人家,父辈说唐姓绝户,如今只留下唐姓人家的老坟,却不见唐姓人家留下的祖屋宅基,唐家大约绝户超过百年。盘姓人口最多,占80%以上。“盘孟王”三姓通婚,盘姓内部十代以上有的通婚,全村便由无亲变有亲,族亲变近亲。亲戚关系错综复杂,村里工作难做,干部难当,每届选举队干部,成为十分困难的事。
我祖上原本不姓盘,姓王,从全州县城湘江边绕山村迁入,改为盘姓,变身瑶人。从相对富饶之地迁入大山深处,祖先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作过多种推测:躲避战火,逃避兵役,过自给自足的自由生活。如今盘姓有十多代人,接近三百年。进入瑶族区域,经过祖先跟瑶民通婚,我们的血液里少不了瑶族血统。
很小的时候,我还能听到爷爷辈偶尔说说瑶话,也能见到外村亲戚穿着瑶服来访。没过几年,我不到十岁,村里几乎没人说瑶话,周边瑶族村庄的瑶服也鲜见。瑶汉文化交融的步子越发加快,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瑶族风俗、汉族风俗,大家有了同样的风俗和方言,过同样的大大小小的节日。
东山瑶族乡属喀斯特地貌的高寒山区,平均海拔800米,各村庄因地而建,错落无序,因而不同地势间有不同的海拔和气温。冬天冰冻,山山岭岭、村村寨寨,厚薄不一,冰雪融化速度有快有慢;插秧收割时间,也会差个三五天,甚至十天。
古时候,也就是三百多年前吧,这个大山区人烟稀少,许多山岭无主,谁占领谁是主人。因路途远,行走困难,开垦不了的山,便以安葬老人抢占。我村有那么几个外村人的祖坟,可能因为他们无力管辖占地,也许因为我村人口逐渐增长,势力加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天,其中一个老坟被他们的后辈迁走。而有的老坟,无人管理,自生自灭。
村口那个老坟至今还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村里有人在老坟边建屋,八十年代中后期,坟主后人不断进村来闹事,说占了他家地盘,要求拆房将地盘腾出。太闹心,这家人被迫到村东北水源山较高山坡建房。那一小块地空出来了,这些年,成为停车场,附近人家搞基建,拿来堆放材料、拌砂浆。
前两年,有一个高中学弟在微信里跟我说,他们祖先曾经在我村生活过,并指出大约在村里哪座山坡上的哪个位置。此历史,我第一次听说。回村时,我特意去寻找,果真有人生活过的痕迹。我问父亲,知道这个事吗?父亲记忆模糊,说似乎听老辈说过。
父亲今年八十七岁,有健康的身体和超强的记忆力,有些事,我都不记得了,他还记得。父亲对师弟祖先曾生活在我村无明确记忆,只能说明,那段往事过去久远,村里一辈辈不再提及,并渐渐遗忘,断了记忆。师弟他们村与我村相隔较远,他还说,多年前,他和几个长辈、同辈特意来寻访过其祖先的踪迹。
大山深处,那些由时空编织的经纬,网住过人类停留或迁徙的印记,呈现出有厚度的历史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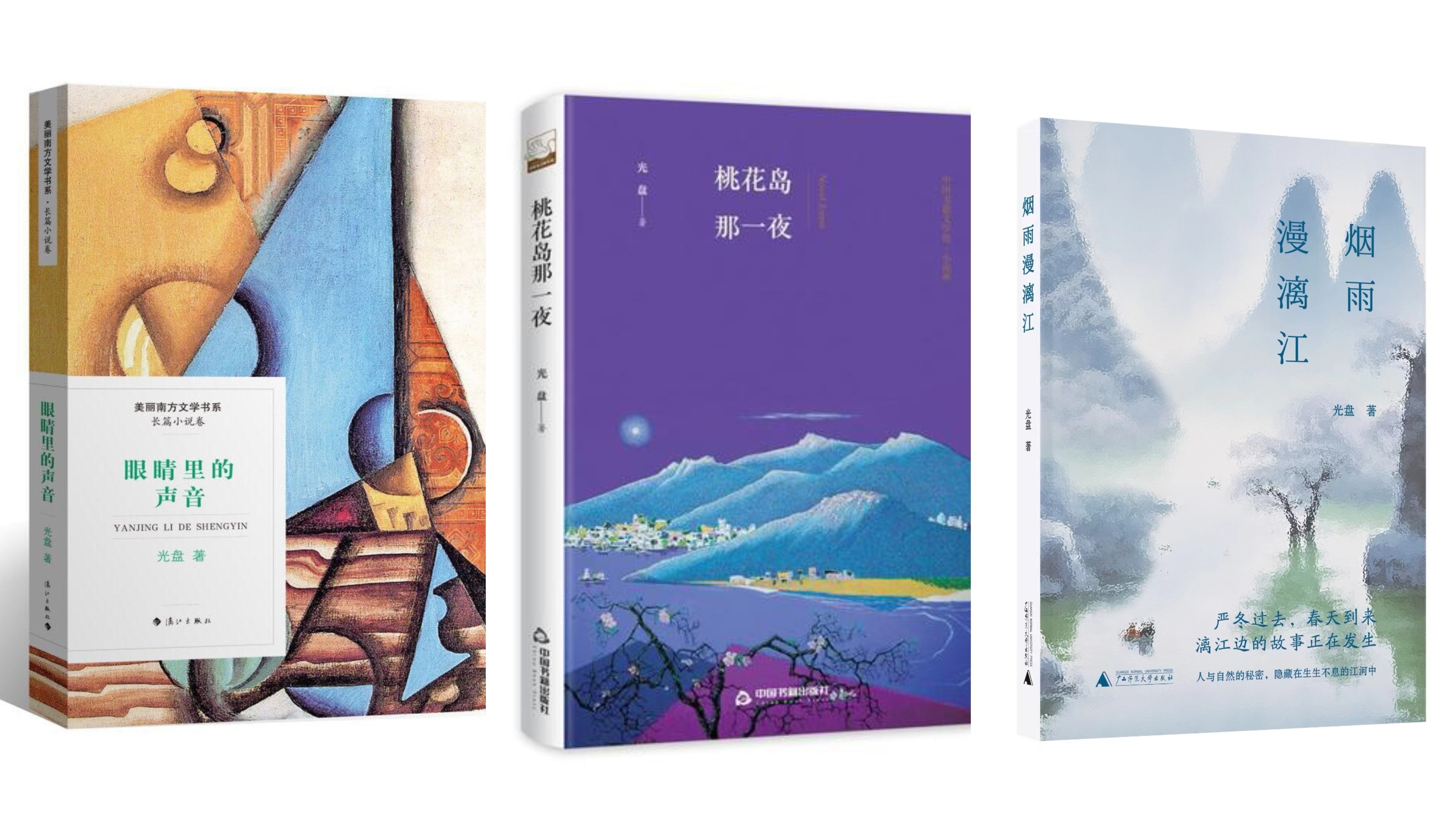
二
祖宗留下好几座依山而建的老屋,虽无口头传说及文字记载,但根据我爷爷辈房屋所有权推测,应在二百年上下。上辈人口少,到了我辈,人丁兴旺。老屋拥挤,父辈纷纷另建住房。随着主人对老屋的离弃,老屋失去烟火,渐渐倾圯,只剩下地基,有的被所有权者建成洋楼。村里的新建筑杂乱无序,没有规划,土地窄小原因,大部分洋楼建得局促、拘谨。
村道早几年有过一次道路硬化,两三年前开始破败、塌陷,烂得不成样子。早些年,村里干部由留守的中年人担任,由于青壮年大都在外务工,干活缺人,村里许多公益事业无法实施。这届干部卸任后,勉强选了年轻人担任村里干部,这几个年轻人在拒绝中勉强答应,却因为长年在外,无睱顾及村里的事。
村子不大,人心却杂,谁也没有信心把村子管理好。届期未满,选出一位留守在村的相对年轻的中年人担任队长,他考虑良久,最后答应。这个叫小禾的新任队长,在远离村子的深山里建了一个养鸡场,全年收入可观。他上任后,争取到县红十字会支持,将那条水流自琵琶岩的自然小溪,建成水泥水渠。不久,小禾因高血压引起的突然中风,离开人世。十分痛心。他还有不少想法,但都没来得及实施。甚是遗憾。
去年底,我专程去参观新水渠。来到琵琶岩,往洞里深处探望,听得有流水撞击岩石的响声,据说,十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小瀑布。蛇年春节期间,我又跟三哥一同去参访新水渠,以示对小禾的纪念,向所有建设者致敬。碰上在地里干活的小弟,他过来陪同,并向我们讲述水渠建设的一些小故事。水渠建设,因劳动力不足,花费不少工。水渠蛇行般穿梭在田垌,一路上有排水灌溉设计;地势低的地方,有地下井水从田里冒出来,为排涝,水渠便在此留下排水孔。水渠工程虽小,需要考虑的问题却不少,目的是让每一个村里人满意。
我村有三口老井,但有两口污染了,人不能饮用。村里用的自来水,取自村舍三里外高处的地下河。取水处是一条狭长谷地,有源头活水,这个地名叫“里头槽谷”。我小时候,集体时代,村里曾在此修建水库,由于技术落后,花掉不少人力物力,最终水库并没建成功。紧连着的下方,地名叫水口岩,有一个不深的溶洞,洞口高大,一年四季能听到明处及地下河流水的声音。水口岩洞前是一个不深的大坑,一条溪流擦边而过,溪道不宽,却不浅,水流不远,便钻入地下。大坑底部,曾经种过田,前端有一个天然的大坝。天然大坝之下便是前面提到的琵琶岩,琵琶岩前是一大片农田,村里主要农田位于此。
琵琶岩洞的水,与“里头槽谷”、水口岩的水一定流入了同一条地下河。当天,我跟三哥设想说,如果在“里头槽谷”重建水库,水口岩新建水库,建成两级水库,再建一条绕村水渠,村里大部分田地都能灌溉。利用水库的水建个小型发电站,条件也具备。
从大处来说,我村也是一座天然水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县里就准备将我村搬离,建一座水库,可刚刚开始建设,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通向地下河的大坑,因无法填补,只得放弃。放弃也许是对的。我村大山背后,那座建于七十年代的弄岩水库,因为水压强大,击穿了地洞,库水与地下河相连,地下河水位下降时,水库水变浅直至干涸。以前水库两三年见一次底,这两年因为干旱,几乎年年见底。
弄岩水库,通过暗河与湖南永州零陵区的排家洞村相连,两地共用一个水库。广西这边,由于没规划好水渠,因而从没享受过水库带来的好处。经过我村的那条水渠,还没使用就废弃了。眼下,弄岩水库广西境内正在重新打洞,建新的水渠。可是,新的水渠规划,并不经过我村,我村只能干瞪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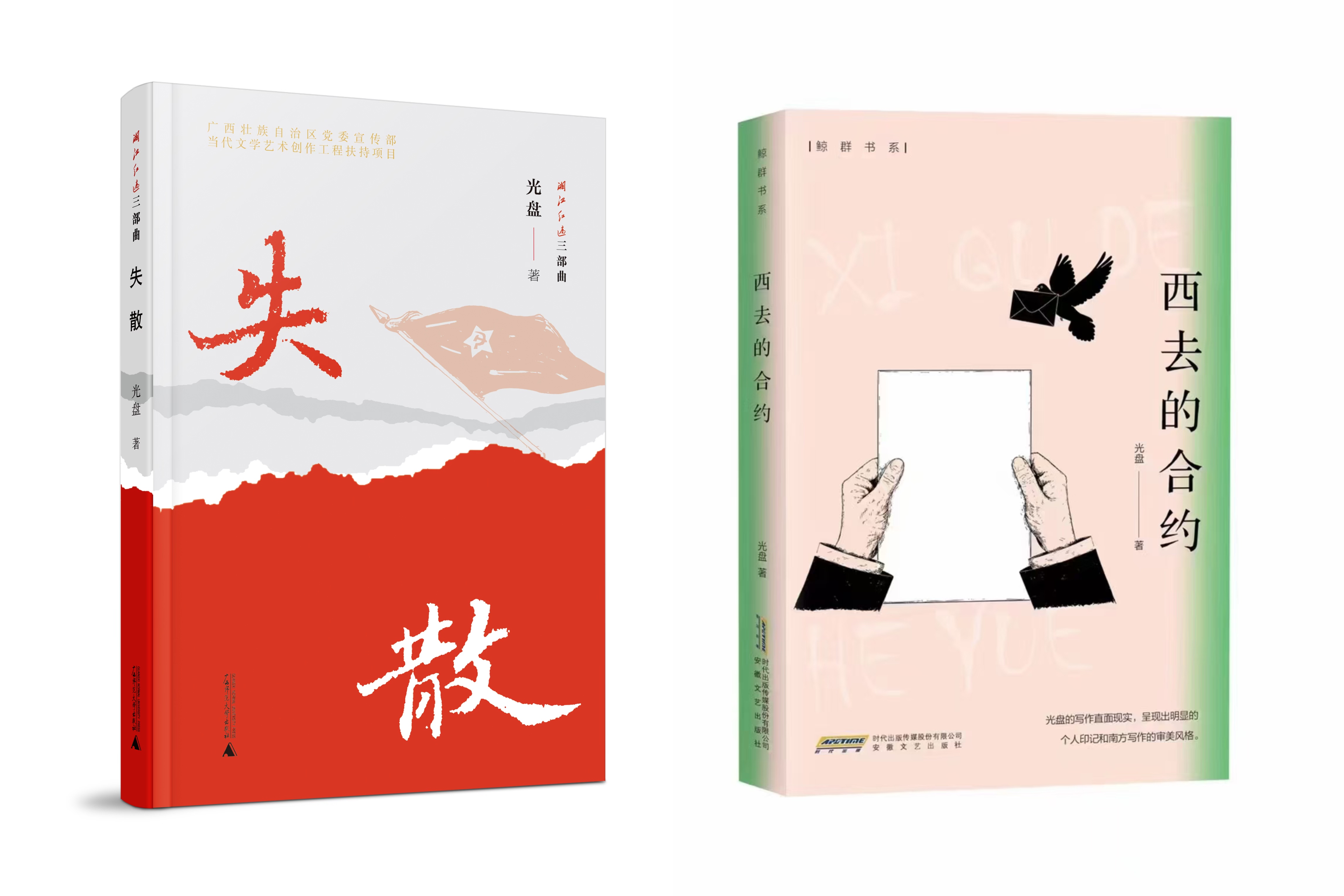
三
村里还有一条流水的岩洞,叫冷水岩。因流出的水冰冷而得名。不过,近年冷水岩时常断流。
这两年干旱,自来水断供,水井水位极低,大前年碰上超过我父亲记忆的大旱,王家开出来的老井(称之王家井眼)仍然没有断流。但饮用,只能用水瓢一瓢一瓢往桶里舀。因为缺水,许多有条件的留守老人离开村庄,暂时躲避。
蛇年春节前夕,自来水又断供了,有人在琵琶岩发现一处新的水源,那水清纯,水流如瓢泼,如此干旱,还保有这么大水量,如果引入自来水塔,一定能对付大干旱年月。有人在村微信群里呼吁,却鲜有人回应。过了些天,务工人员陆续回村,又有人呼吁,却因为小禾去世后,村里缺队长,没人组织牵头,终究没做成。不几天,下了两场大雨,地下河涨了,自来水丰富了,村里人忘记了干旱,重新引水之事再无人提起。我回村里,经过水塔,见溢出来的水,正通过一条水管放掉。哗啦啦的,放掉很可惜,但不放掉,眼下又无用处。
喀斯特地貎河流溪水不多,大部分水都存留在岩石之下。我村也是这种情况,水资源丰富,却没有科学开发利用。我和三哥建议策划、评估、重建、新建水库,没得到任何响应。大概吧,缺带头人,缺资金,缺人力。村里青壮年只盼着快点离开,去到城市,去到能赚钱的地方。他们的“快餐文化”我能理解,在乡村,想干成一件大事,特别困难。眼界,资金,胆识,组织能力,样样都缺。将心比心,我也缺。因此,徒留叹息。
感情联络方面全村从未间断。村里红白喜事,家家都要去礼,谁过大寿,全村人随礼祝贺。村里有人过世,无论多远,无论干什么工作,青壮年都会及时赶回来帮忙。
我不太喜欢村里人不间断地走动和没有完结的吃喝应酬,但我骨子里又欣赏甚至享受这种亲情及亲情文化。
四
故乡多雾,有时雾浓如烟。浓雾天气,人在田地里干活,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小时候放牛,牛野性来了,满山满岭跑,放牛娃贪玩,等想起赶牛回家时,牛不见了,急忙翻山越岭寻找。作为放牛娃,不可赶着牛出门空着手回家,那样会被同伴讥笑,遭家长怒骂。几乎每头牛都有一个名字,牛相貌主人能一眼认出,碰上浓雾天气,唤着牛寻找,怎么也找不到。待到雾薄,才发现,牛就在那里,它有意不搭理你,跟你对着干。
不过,雾多的地方,空气湿润,人的肤色也好。春节前,我皮肤干燥,脸上起皮,涂抹了十来天护肤霜都治不住。往年不是这样,往脸上抹个两三天,皮肤就光滑了。桂林不是干燥之地,今年特别怪。我猜想,与年纪大了有关。被父亲催促回村,吹过故乡的风,喝过故乡的水,呼吸过故乡的空气,第三天我回桂林,不涂抹护肤品的脸,湿润而滑爽。
总体来说,我讨厌故乡的浓雾,并把这种讨厌埋入心底。讨厌浓雾,源自要在浓雾里寻牛、干活。少年时我固执地认为,村里穷,家里穷,都是因为雾浓,雾浓是因为连绵不绝的高山。山多且高,通向外界的路就艰险,离发达地区及富裕生活就遥远。
十来岁时,听婶娘说,上面准备搞人造平原,村里的山岭都要炸平。我信以为真,盼望了许多年。憎恨贫穷和大山,在长辈那里也普遍存在。正是这种观点引导,我从小便厌恶故乡,一心想逃离。
小时候,村里人羡慕招工出去的人,那些进入城市者如坠蜜缸。有一个表姐被招工进入桂林糖果厂,她回村探亲时说,桂林城里的人生活好富裕,吃不完的饭菜统统倒掉。不吃剩饭剩菜,那是多大的浪费!村里人感到不可思议。每个复述者,都咂巴着嘴,个别没出息的人,听着或讲述着口水流得老长。这更加重了我逃离故乡的心思。
如今,年纪增长,见识多了,终于明白高山大川存在的好,它调节气候,孕育水源,还能保证生物的多样性。人年纪大,才能真正体会到故乡之暖,故乡之爱也会深沉,从容。
五
集体劳动时,村里偷拿集体财产的人不少。丰收季节,比如扯花生、挖红薯、摘辣椒,劳作者趁人不备将上述物品私藏于身。也有人藏在回家路上的草丛里,待半夜悄悄去取回来。有时,偷窃者回取赃物时能碰上,大家假装看不见,假装不知对方在干啥,然后相互隐瞒。我心思重,虽不会揭发偷盗者,却十分讨厌偷盗行为,只想立即离开村庄。接到考入县中的通知,我便知道城市已经向我招手,逃离乡村有望了。
成家立业后,好几年我都没有回村。那时父母年纪还不算大,他俩常到桂林看我。父母名义上看我,实则来要钱。父亲不当赤脚医生了,没了经济收入,泥土里又很难刨出银两。大哥二哥三哥都在乡镇当干部、当老师,父母平时“麻烦”他们太多,所以只能久不久来“麻烦”我一下。
那时,两个年龄相差较大的妹妹还在上学,需要“巨额”费用。当年,农村最怕上学、生病,这两样重担往往能压垮一个家庭。到了桂林,他们也不出门,带他们游山玩水,他们不感兴趣。但只要我给了钱,他们便立即找借口回家。我摸清了父母的意图,以后每次一来,我就主动把钱给母亲。接过钱,母亲浑身不安,直到我说你们想回就回吧,她这才绽放笑脸,安心吃喝,当天,最多次日,赶车回家。
年轻时,我借口交通不便,很少回家,也极少带妻儿回老家。后来,有了私家车,通往村里的公路硬化,我仍不爱回家。子女大了,父母总是希望子女多回家看看,但父母对我特别开恩,我回家少,他们不怪罪。即使回到家,我也跟家人说话少,跟村里人交流少。内心深处,还是对曾经带给我苦日子的乡村有抵触,用沉默、精神逃避来对抗。
乡村一天天变化,当今形势下,不外出务工,只要勤劳,脱贫不是问题。但说到真正振兴乡村,还有一段路要走,还需要摸索路子。振兴乡村首先需要人,尤其年轻人。而长年待在城里的年轻人,跟我一样,大都不习惯乡村,哪怕收入低,也不愿回乡村发展,更何况乡村大都没有理想、稳定的产业。
城市扎不了根,乡村不愿回,他们在矛盾、迷茫中一天天过着日子。开展爱故乡教育,有没有用呢?也许有用,我想,口头上的教育,效果不会明显。以什么来吸引农村青年回乡创业,应该是一乡一策,甚至一村一策,不可复制照搬。同时,我认为,用行动爱故乡,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从自己身上看村里的年轻人,对他们充满信心。总有一天,他们会自觉地爱故乡,自觉地建设故乡。他们在外闯荡的经历经验,对未来建设家乡必定有极大帮助。
当年,小弟就是这样。两口子在外务工数年,带着不舍、不服回到村里。刚回家那阵,有许多发家致富的想法。他曾经因担心失败而害怕创业,在外经过几年风雨之后,已克服掉害怕心理,变得果断有胆识。最后,他选择建养猪场。不出三年,小弟两口子闯出了一条路子。
目前,村里有五六家人搞养殖,虽然累,也担着风险,但都坚持了下来。他们不只养殖,还种植,种槐花,种豆角,种辣椒,种红薯,种花生,种玉米……每一个品种收入不高,累加起来,收入就理想了。他们总是那么忙碌劳累,却异常充实。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目标很小,每年都能实现;只要农村政策稳定、对路,他们思想负担就很轻。
村里留守人员虽少,但因为有耕种,有收获,有创业,有对美好生活的无尽向往,仍然生机勃勃。
如今,母亲不在了,父亲健在。父亲就是我的故乡,他在,故乡便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系着我,我无论如何逃离,都别想逃掉,还会不可自控地回望并踏上回乡的旅程。
作者:光盘
名家简介:光盘,本名盘文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广西作协原副主席、桂林市文联副主席,广西文坛“后三剑客”之一。著有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失散》《英雄水雷》《眼睛里的声音》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光盘卷》《桃花岛那一夜》《野菊花》《西去的合约》等。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广西第五、第十届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小说《赴那个十八岁的约》《必须掉头》等改编成微电影、电影。
服务邮箱:agricn@126.com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4395205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354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170078 京ICP证05068373号
农民日报社主办,中国农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2019-2025 by farmer.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